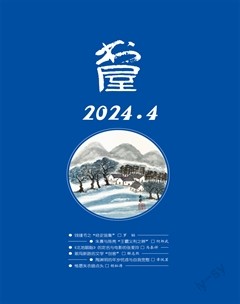在古典诗歌里,义山诗堪称最难读懂,意象纷繁、境界朦胧及指涉心灵世界,是其诗旨多义且模糊的因由。品读李浩的诗集《奇迹》(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印象即是精致深刻到难以清晰复述主旨,其诗对义山诗是否有过借鉴不得而知,但两者对诗体精雕细琢的精神却是相通的。恰如弯弯绕绕的迷宫,对于走马观花的读者来说,很难找寻到出口,但只要潜心细读,定能发现探秘过程的巨大吸引力,以及千百度辗转后蓦然间走进诗人内心的喜悦。汲取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抒情传统中的养分,并从西方现代诗歌里不断获取力量,李浩持续进行着新诗神圣性的拓宽、深化。捕捉李浩诗歌中的遣词造句、结构主旨,孤独、灾难、救赎、死亡、生命这些灰暗色调的语词常常出现,而贯注其中的是诗人长久以来抱持的悲悯情怀。
推求诗歌题旨,有显与隐两极,相较于诗旨的直白显豁,幽微深远者应更能于读者心中产生持久的涟漪。当我们初读一首极难懂的诗,囿限于学识积累、人生阅历,或许会感觉到陌生和距离感,但随着境界的不断提升,感知隐微深邃的能力,以及直击灵魂深处的共鸣会让人欣喜不已。《雪》叙写诗人观雪时的心境与感想,寂静飘落的雪花彰显极致的孤独,“你知道的,‘这一切,是那么多余,多余的,叫人相信死。’可是/我还是迷信爱。我孤身一人走到/夜晚的尽头,这路程多像森林!”,触景生情,在死与爱间沉思并抉择。《在林中》通过刻绘梦中场景,诸如“这些树好像大地的使者”“死者的嗓音和怨恨”“确实有死去的幽灵”,细味幽思文学主题中亘古既久的死亡书写。《私人日记》中将很多蕴含深意的意象进行叠加,“白雪上冻住的猪蹄爪”“路边堆满牛粪的麦田”“躲在塘坎茂密的刺丛中/和洞穴里会跑的野鸡、黄鼠狼、土拨鼠,/还有兔子和土狼”,共同构成了中原乡野的独特风景线,景致之外,这片土地上那些艰难生长的灵魂滋养了诗人复活了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