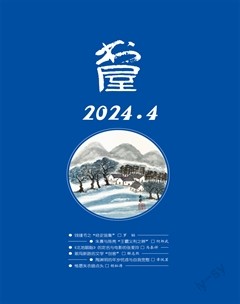近来编了一册关于书的文集,本拟名为《书话集》,想起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对书话的阐述,乃是“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并被热爱书话的朋友奉为圭臬。作为也曾自以为写过几册书话著作的作者,我读唐弢先生的这个对于书话的定义,感觉颇有道理,但对比时下各种书话作品,却总是觉得不是滋味。由此想来,书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可以看作关于书的纪事,关于书的闲话,关于书的掌故,以及关于书的趣闻,这也便是唐弢先生所说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对于热爱写作的朋友来说,写作书话,其实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有无这“一点事实,一点掌故”。真正的书话写作,其实并非人人可为,掌握这些“事实”与“掌故”的作者,或者是编辑家、出版家、藏书家,甚或是极有情趣的文人学者。而由此,书话,也才能成为他们在闲余之际所写的一种特别文章。我以为很少有专门的书话家,因为关于书的“事实”与“掌故”毕竟是有限的。作为藏书家的黄裳先生,晚年也常常会为写文章没有材料而苦恼。书话作为一种文体,又因为这“一点”的缘故,多是短的,很少长篇大论;也因为“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又是言之有物和活泼可读的,而绝不是堆砌材料的八股东西。
谈起书话,首先想到《晦庵书话》。那么,不妨先来谈谈这一路的书话写作。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著名杂文家,而他的另一个醒目的身份,则是新文学版本的收藏者。唐弢的新文学版本收藏极为丰富,现代文学馆的藏书,或有半壁为其捐赠,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印制了《唐弢藏书目录》作为纪念。这几种特殊身份的叠加,让唐弢在写作书话时能够游刃有余,谈书作文颇如囊中取宝,而先生又总是平静而克制的,那抒情的气息是淡淡的,令人如闻清香。这才是真正读书人的神采。继承唐弢新文学书话写作衣钵的,是供职于《人民日报》社副刊的编辑家姜德明先生。姜先生对唐弢先生极为追慕,除了大量收藏新文学书籍之外,姜先生还善于交游,并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姜先生散文写作十分活跃。此外,姜先生早年还专门研究鲁迅,并曾就此写过一部研究鲁迅的书话作品。无论是唐弢先生,还是姜德明先生,他们的书话写作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他们能够对掌握的材料迅速做出精准判断,从而写出一篇篇隽永有味的短文。我把他们看作藏书家一路的书话家。
或许是唐弢先生的书话太有名气了,追随者众,但有大成就者少。黄裳曾写过《拟书话》,便是对唐弢的书话体文章的仿写。作为著名藏书家和散文家的黄裳,按说是可以就此写出一大批的“书话”作品来的。黄裳主要收藏明清珍籍善本,他的关于藏书的文章,却少以“书话”来命名。其最有代表性的谈书文集,一本为《书之归去来》,另一本应为《来燕榭书跋》,这两本书都是他人难以写就的。前者写他收藏古籍珍本的经历,有得书的喜悦,又有失书的沉痛,颇有“沉郁顿挫”之味。得书之作,有《西泠访书记》《姑苏访书记》《湖上访书记》等多篇,皆为云霞满纸的好文章。失书之作,则有《书之归去来》等多篇,还有篇谈他购读《药味集》后又意外失而复得的故事,堪称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