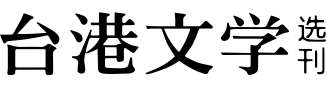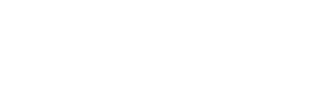月 娘
本地方言里,把月亮唤作月娘。
今晚的月色很白,像梨花白,白烁烁,纯净而有光泽。照着村子的山林田地、屋舍村道。中午刚落过一场雷公雨,涮去了天地所有尘垢。天空一片普蓝,几缕稀淡的云彩闪在天边随风飘忽。
这是农历的冬月十六,圆满的月娘早早出来了。
月光照着一座农家老厝,外观陈旧破损。双扇大门一边高一边低,土夯的院墙早已经倒塌,成了一道土坎,露出几块光滑的基石卵。四房一厅和两边厢房,还有半边的辅厝,架构还在,只是屋瓦不整,四处漏下粗细交参的月光。西厢房较长,有两个门,一个进睡房,一个进厨房。相隔院埕的东厢房却短了一截,为了让位给大门,只剩下一小间;作为客房,有时有人住,有时放空收杂物。
這夜,东厢房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妻。看款式,外表青涩,内在深沉,说是下乡来闲逛的。这时际,那对后生人不出去看月色,却躲在屋里,透过木窗格,窥探着西厢房的一举一动。
西厢房住着的是一位年迈的老阿婆。老阿婆先是在厨房里忙了一阵,而后颤颤巍巍走出来,坐在房外过道的条凳上,背靠着墙板壁。条凳上放着一只火笼,脚底下还躺着一只毛色黑白相杂的大花猫。月光明晃晃地照着老阿婆的身躯和头脸。老阿婆的身材修长,穿插规整,上身是老款式的深蓝色大褂,下面穿一条滚了花边的黑色裙子。像中堂古画上走下来的祖宗人物。头上的毛发白得耀眼,脑后挽个发髻,好像刚抹过当年新榨的山茶油,亮铮铮。老阿婆的脸盘端庄清癯,布满了细细的丝瓜络般皱纹,看那脸型和气色,与天上的月娘一般。
东厢房的年轻夫妻看得发呆,悄悄发议论。
女客说:没错,她就是月娘婆。看那身材,年轻时,肯定是美女一个。
男客说:下午来时村长就说过,月娘婆是村里的五保户……
女客说:可惜红颜薄命,怎么会孤单无后呢?
男客说:免你烦恼,一年四季,柴米油盐,村里全包了,食用无欠……
柴米油盐有了,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哪。女客还在替老阿婆惋惜嗟叹。
你尽管发慈悲,我去找阿婆说闲话。男客说着,出了房门,径直倚近西厢房阿婆面前。
这时,蜷伏在阿婆脚下的花猫,见来了生分人,一窜,钻进主人的怀里。
月娘婆正闭眼沉思,嗫嚅轻声叨念什么,被来客和猫扰醒了,开口连续发问:人客,食了未?没出去走走啊?听口腔,你也是在地人啊?你做囝仔时候也会念歌吧?
男客连连点头,说:阿婆,搅吵了。你说念什么歌呢?
阿婆说:你会念《月娘月光光》吧?
月娘月光光,起厝起花园,爱吃三积糖,爱困新眠床。新棉被,无虼蚤。新蚊罩,无蚊吼。囝仔要睡不能吼……是吧?男客说,我做囝仔时若睡不着,阿妈就会念给我听。
阿婆说:是的,现时我都念不出来,忘去了,老颠了。
男客问:阿婆今年高寿啊?
我也记不清了。月娘婆笑笑,拍拍怀里那只花猫的头说。算起来,不知道熬过了多少年,熬过了这只猫的前三代,又熬了它十几年了,快熬到头了吧。
男客说:早哩,我看阿婆眼珠光,耳朵利,福气还在后头哩。
月娘婆说:少年郎会说话。看你大城市住住,乡社走走,翁婆成双结对,很清闲咧……
说得男客红脸赤耳,托辞踅回东厢房去了。
月娘婆依旧独自坐在条凳上,背靠着板壁。她把花猫赶到脚下,把火笼揽在怀里,似睡非睡,好像在看天上的月娘,又像在等什么人 。
这时,门前的圳路上走来一个老者,看样子,高个子,步子大,佝偻着腰,胸前揽着火笼,笼里的炭火不时被风吹起几点火星乱飞。
月娘婆看见了那身影。她知道,他来了。不由挪动身子,好为那人让出座来。
“吱呀”一声门响,来人进了大门,走到月娘婆身边,二话不说就坐下了。
月娘婆说:大水流破布咧,现时才到。
来人站起来,掀开自己头上的羊毛帽,光秃秃的头顶袅袅冒起一团白雾。他说:你看我走得头都出汗了,还得你埋怨,你灶脚里有火炭吧。那人说着,自己到厨房,熟门熟路,给自己的火笼添加几块煨红的茶仔壳火炭,那炭耐烧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