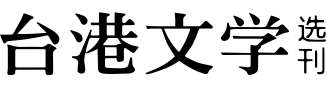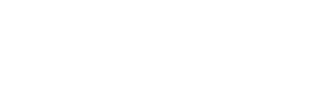陆 经
景祐元年春,对陆经来说,暗含着诸多的玄机。刚过十六岁的他从洛阳赶来汴京,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科考是天下学子的一个梦,但无疑分为好梦和噩梦,要么是金榜题名,要么是名落孙山。陆经是幸运的,他中了是年张唐卿科进士,同榜及第的还有苏舜钦、柳永、龚鼎臣等。陆经和苏舜钦很快成为知己。见诸典籍的,陆经曾向苏舜钦讨教书法上的用笔问题,因此,《宣和书谱》说他与苏舜钦“笔法亦仅同一律”。大多的时间,他们在一起游历、访友、喝酒、谈诗,关系极为密切。也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后,陆经陷入了苏舜钦的“奏邸之狱”,也叫有难共当了。
陆经的命途也够坎坷的了。他原本是越州人。越州,也即当今的绍兴。后来寓居洛阳。之所以这样,其中寓含着曲折和心酸。陆经年幼时,他的生父病逝,其母改嫁洛阳陈见素,改了姓氏,陆经一度成为陈经。陈见素可能是个小官儿,与富弼有交往,关系应该不错,陈见素死后,是富弼作的墓志铭。陈见素死后三年,守孝期满,随复归原姓,陈经又变为陆经。
在洛阳的数年间,陆经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欧阳修。欧阳修也正年轻,在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他们常结伴游龙门,登嵩山,赋诗饮酒,结下很深的友谊。从欧阳修那里,陆经真正理解了做文章的奥秘,开始大量阅读韩愈的作品,一些经典的篇目,不厌其烦地诵读,有的甚至都能背下来。同时,开始问津诗歌的写作。明道元年,陆经与欧阳修再游龙门,欧阳修诗兴遄发,写下了《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后来全收录在了《欧阳文忠公集》(卷一)里面。陆经也写了诗,回去后感到很稚嫩,一冲动,全给焚烧掉了,没能留下只句片言。很是遗憾。
中进士后,陆经没像其他人那样,到地方上出任县尉或者主簿,而是留在了汴京,做了一个小小的校书郎,这也许是沾了年龄小的光。十六岁登进士甲科,无论怎么说,在朝野都算得上热点了。他的同年、好朋友苏舜钦就没他幸运了,外放出任蒙山县令。直接到地方上做县令,这和苏舜钦的家庭背景和阅历有关。因为父亲的原因,苏舜钦早年靠荫补步入仕途,先是在京城做太庙斋郎,后又改任荥阳县尉。可有一天苏舜钦突然辞去官职,闭门苦读,立志定要金榜题名。北宋有一个惯例,靠荫补取得官职的人,很难走到重要的职位上去,苏舜钦是有远大抱负的。
然而,抱负还没来得及施展,苏舜钦就身陷“奏邸之狱”,被削籍为民,编管苏州。作为苏舜钦好朋友的陆经也参加了那场酒会,自然受到了牵连,责授袁州别驾。陆经一点不后悔交到苏舜钦这个朋友,不顾别人劝阻,执意与苏舜钦结伴南下,经苏州再赴袁州。一路上,二人吟咏唱和,互相勉励,排遣孤独和烦恼。“所乐与君共,已忘窜逐伤。”友谊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苏舜钦《维舟野步呈子履》中的诗句,也是陆经的心声。
在偏远的袁州,陆经一待就是近十年。可以想见,这十年的日子不好过。之间陆经曾寄诗给王安石,尽管所寄之诗没能流传下来,但从王安石的答诗:“直使声名传后世,穷通何必较功勋?”可以看出,陆经向王安石诉说了自己的穷困潦倒,并为“奏邸之狱”鸣冤叫屈。此时的王安石也只能在精神上勉励陆经,希望冤案早雪,返抵帝都,成就千秋伟业。
陆经十年贬谪,似已被朝廷遗忘,那么一个低微的官职,俸禄低得可怜,生活到了极其困窘的地步,而且精神上还遭受着摧残,世俗的冷眼和嘲刺,无日不在重复上演。这一切的一切,有一个人感同身受。这个人就是梅尧臣。陆经与梅尧臣的认识,也应该是经欧阳修介绍的。康定元年,陆经升官了,同时,一纸诏书,让他参与到《崇文总目》的编纂行列,与欧阳修成为同事。欧阳修与梅尧臣是好朋友,介绍他们认识完全在情理之中。梅尧臣亦多年落魄失意,与陆经可谓是同病相怜。因此,他赠诗给陆经,曰:“陆郎谪去十年归,长乐钟声下太微。屈指故人无囊日,平明骑马扣吾扉。论情论旧弹冠少,多病多愁饮酒稀。犹喜醉翁时一见,攀炎附热莫相讥。”此中还提到了醉翁欧阳修,两个失意的文人,幸亏还有一个官高位尊权重的欧阳修。
若算起来,陆经和欧阳修的交往,要早于梅尧臣与欧阳修的交往,更早于尹洙、苏舜钦、江邻几等人与欧阳修的交往。这几个人,全可称得上是北宋悲剧式的人物。然而,无论这些人生前如何,身后可都是留得了千秋美名,很大程度上,多与欧阳修有关。欧阳修和他们的唱和、交游、品题等等,都得到很好地流传而广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陆经呢,欧阳修与他和诗最多,而且多次铭其藏、序其文,不输以上诸人,却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近千年来少有人问津,遂使美名不传。有人责怪苍天不公,其实不然,陆经也许视这些浮名如粪土,诗文随作随丢,不然,为何会没有《文集》传世?
陆经这一生,注定是和欧阳修难相分开的。当年,那场“晏太尉西园赋雪”事件,陆经是亲身目睹者,他认为欧阳修没有错,边境狼烟正浓,士卒浴血疆场,作为一国之宰辅,还要对雪饮酒赋诗,怎么还会有如此雅兴?欧阳修当面不好拒绝,却在诗中讽刺了晏殊。从此以后,师生二人的关系就淡了。晏殊曾在背后贬毁欧阳修:“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陆经觉得晏殊很无聊,很替欧阳修有这样的老师而悲哀。
知颍州时,陆经与欧阳修再次相聚。欧阳修罢去参知政事一职,出知亳州。赴任途中,想起陆经在颍州任职,便绕道颍州去与陆经相会。老朋友忽然如同天降,陆经异常高兴,拿出珍藏的宋仁宗飞白书法真迹让欧阳修赏阅。欧阳修颍州偶染小恙,陆经亲开药方,令家人去药铺抓药,亲手煎熬,以調羹喂欧阳修喝下。病好后,欧阳修连写《答陆学士经》数首相赠。颍州期间,欧阳修还写了十三首《思颍诗》,陆经亲手书丹,找来当地刻碑名匠,将这十三首诗勒石传世。欧阳修写给自己的那几首诗,却藏在书斋的布囊之中。后来,就失去了踪影。
唐 询
凡是收藏砚台的,都应该知道唐询这个人。他著了一部有关砚台的书,叫《砚录》,对砚的石种、质地、形状、渊源以及掌故等都有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北宋与宋之前砚台的重要史料。
对于砚石,唐询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癖好。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砚墨纸笔等文房之物,而且很挑剔,他自己说,墨纸笔,必拣最精良者去购买,挥洒之时,方能心手双畅,如入无人之境。但四者之中让他选其一,那他宁愿舍弃墨纸笔三物而独取砚之一物。“至于可爱终身,独砚而已。”这是唐询《砚录》里的话。
这话主观色彩浓了一些。就像齐白石说的,我诗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就看怎么去理解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不能挨字眼去抠。抠到最后,抠成了一钵糨糊糊。
唐询收藏的第一方砚,是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方端溪石砚。这方砚很小,还不足四寸大,上圆下方,可以窝在手里去把玩。但这却不是一方普通的石砚,砚池当间有鸲鹆眼,是端溪砚中的上品。端砚素有“无眼不成端”之说。然而,“眼”又分三六九等,鸲鹆眼之下,更有鹦哥眼、鸡翁眼、麻雀眼和象眼等。唐询的这方端砚,不仅有鸲鹆眼,还有两丝金线若隐若现,这就更是不容易见得到了。
这方砚揭开了唐询的觅砚之路。《砚录》里有详细的记载。譬如,天圣八年礼部省试的时候,见贡士茹孝标携一方黄石砚,色不甚深,但显得很沉着,正圆形,比他的那方端溪石砚还小一点,发墨极好,墨光可鉴人耳目。问是从何处得来?云:“出自新罗国。”北宋时的新罗国,就是现在的韩国。再如,书坛有一公案,与砚有关,自然引起了唐询的兴趣。《砚录》中记载了这件事。南唐李后主留意笔札,用具精良,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此三者,为天下之冠。
可惜,南唐亡国了。
亡国之后,龙尾石砚也随之销声匿迹,成为一桩悬案。唐询多次想揭开这一谜底,可惜都没能如愿。这样就到了仁宗景祐年间。校理钱仙芝出知歙州,唐询得知音讯,即修书一封,拜托钱仙芝寻找当年李后主取石之处。取石处是找到了,却被滔滔溪水所淹没,且溪水深不可测,人迹不能至。其时,唐询在诸暨做县令,赶来歙州,说动钱仙芝导溪水改由别道,遂得佳石,龙尾石砚再度问世。
为寻觅砚石,唐询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到得一地,他都会轻车简从,去深山古刹,偏远村落,了解当地历史风物、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其实,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心,全在砚石上面。
庆历二年,唐询知归州。归州西南十余里,有一处浩淼的水域,当地人叫它昊池,其实是江水在这里穴一个湾形成的。昊池里有一种石头,当地人偶尔会拿它来制作砚台。唐询得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等进入冬季,昊池里的水干涸了,唐询就组织工匠取石琢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