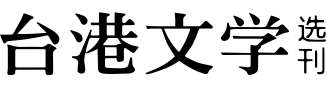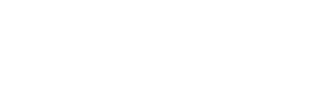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卅四)陈文岩咏姜夔
倚声几个律能分,白石①当推第一人。
自度曲成新定调,韵高境邈不沾尘。
①姜夔号白石。
秦岭雪:同周邦彦一样,姜白石也是词人、音乐家,能创调制谱。姜白石向朝廷献过《大乐议》《琴瑟考古图》。他的词集中标有工尺谱的有十七首,是非常珍贵的数据。
《大乐议》是词乐的专业论文,姑引一句:“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
工尺谱,在外行人看来,有点像以前的普通话注音符号。对这些符号还很有争议,现在懂这门学问的人很少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云南大学刘尧民教授著有《词与音乐》一书,可谓空谷足音。
词律比诗律复杂得多,朱子当时就不大了了。据说,宋朝并无固定的词韵。现在要复原宋人的词调,恐怕得起柳永、周邦彦、姜白石于地下,并把当时的乐队、歌女一股脑儿请来。因此,对词律的讲究只能在一个很粗浅的水平上,认真起来,许多名作会被指为“不通”。
周邦彦中了进士,还有官当。姜白石却是场屋困顿,终身布衣,依附有钱的官僚朋友,流徙江浙一带,是为清客。他又负有才名,不仅诗词,文章、书法都很了得,但“文章憎命达”。据说,他身后也很萧条,无以营葬。这与柳永有点相似。
如此身世,表现在作品中,时时就很消沉郁结,甚至凄清。他几首名作都写于冬季,都有“清、寒、冷”这些字样。如【扬州慢】作于冬至日:“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而《暗香》写于辛亥之冬:“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这种种冷感,再加上西窗暗雨、迷蒙月色、哀怨琴声、参差杨柳、梦里幽人,就构成了白石词的基调。他不为浮艳之词,也力避俚俗,追求醇雅。他总是倚着梅花,孤独地吹着玉笛,寻找知音。
同所有讲究“雅”的词人一样,姜白石也喜欢“使事”,即大量使用典故,也叙述自己的故事。但他运用“虚化”的手法,就是不那么贴实(词论家称为质实)。如《疏影》咏梅,用了寿阳公主梅花妆的典故。他不直接写梅花落在额头上,而是说“犹记深宫旧 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有点轻俏,有点迷离。回忆自己与合肥琵琶女的恋爱,留下二十几首情意绵绵的佳作。但读者很难捉摸到具体的生活情景。他只是恍恍惚惚,深情言之。有时甚至是在梦境中出现:“分明又向华胥见”、“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虽然“使事”,又避免琐细的直接的叙述。他用晕染的意笔,将“事”化为描写和抒情,也就有了空灵之感。
白石的词是有故事的,读它如同美文一般的长短不一的词序可知。今事、古事、今日之环境心迹如何“串烧”就大有讲究。对姜白石,铺叙即柳永与东坡的传统,是一法。如【扬州慢】由今及古,荒凉与繁华对照,一目了然。另一法就是跳接、倒置、种种情景交叉,在一种特定的情调中流转。如《暗香》,二三句一转,从我吹笛到玉人摘梅,又转到叹老,说及今日之华筵。下半阕先言想寄梅,再说夜雪,又回到对酒思念:“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最后感叹时序迁移,落花飘零,人、情、景反复迭现。另一首咏柳的《长亭怨慢》也是如此。善于转接,令人有一种新奇的曲径通幽又复朦胧惝恍之感,这是白石词的一大特色。但因此也就容易陷入晦涩的泥淖。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这一些短章。
“雅”是南宋末期词坛的潮流,也是姜白石作为文士清客的习性,包括品格和文风。他也偶有慷慨激昂之作,如与辛稼轩唱和的【永遇乐】。言恢复只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与原作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大异其趣。他还有一首咏巢湖仙姥的【满江红】也用了赤壁抗曹的典故,词曰:“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我想,他即使想到苏东坡也不会说“强虏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