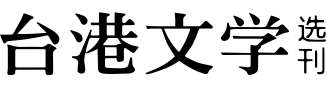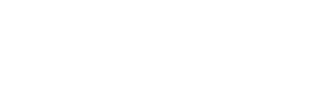洛夫:只见镜中一片空无
人生的净洁,皆在于心。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故云救世必先救心。洛夫的诗,凝神于心,禅意沛然。
有人说,洛夫是在禅诗的“百代之衰”之后,重又复兴了禅诗,赋予了禅诗以新的魅力,因为他的现代禅诗经历了西方现代哲学与超现实主义的洗礼,并将禅诗诗学发展成为“一种生命的觉醒”。
无疑,这里的“生命”,不是指狭隘的个体的生命,而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生命,一种博大如宇宙苍茫的生命。这种生命在禅诗里,应是一种自然的呈现,在表达方式上,排斥使“我”与“物”相隔的阐述或抒情,诗境中诗人晃动的身影愈少愈好,王国维所推崇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可谓这种追求的最佳境界。
在篇幅上,洛夫的现代禅诗与古典禅诗一样,简练简洁,有着清晰的结构。他主张不能让过多的语言排列,影响了生命瞬间“觉醒”时的清新。
洛夫的诗的那种禅意,常常伴着点厌世感、空无感,以及恍然感。他曾在给自己孩子庆贺生日的诗里这样说:世界乃是一断臂的袖子,你来时已空无所有。对这世界的描述真可谓冷而厌呀!所以他的诗,你初读时,迥然四顾,天际茫茫——“抬头只见镜中一片空无”。由此,合成了洛夫独特的“冷与厌”,独到的“空无”,独具的禅意诗魅力。细读,更觉他的确心若明镜,鉴照着这“空无”着的世道人心,或说鉴照着这世道人心的“空无”。明镜能照物,明镜无流滞,常寂常照,三际空寂,究极而论,镜实无知,心果若是之无知乎?妙禅于此乎!
附:洛夫的诗(五首)
洛夫(1928—2018),祖籍衡阳市衡南县,著名诗人,被诗歌界誉为“诗魔”。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魔歌》(1974)、《众荷喧哗》(1976)、《因为风的缘故》(1988)、《月光房子》(1990)、《漂木》(2001)等,散文集《一朵午荷》《落叶在火中沉思》等,评论集《诗人之镜》《洛夫诗论选集》等,译著《雨果传》等。
烟之外
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
已在千帆之外
潮来潮去
左边的鞋印才下午
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
六月原是一本很感伤的书
结局如此之凄美
——落日西沉
你依然凝视
那人眼中展示的一片纯白
他跪向你向昨日向那朵美了整个下午的云
海哟,为何在众灯之中
独点亮那一盏茫然
还能抓住什么呢?
你那曾被称为云的眸子
现有人叫做
烟
金龙禅寺
晚钟
是游客下山的小路
羊齿植物
沿着白色的石阶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处降雪
而只见
一只惊起的灰蝉
把山中的灯火
一盏盏地
点燃
洗 脸
柔水如情
如你多脂而温热的手
这把年纪
玩起水来仍是那么
心猿
意马
赶紧拧干毛巾
一抹脸
抬头只见镜中一片空无
猿不啸
马不惊
水,仍如那只柔柔的手
——一种凄清的旋律
从我的华发上流过
因为风的缘故
昨日我沿着河岸
漫步到
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
顺便请烟囱
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
稍有暧昧之处
势所难免
因为风的缘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
赶快发怒,或者发笑
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
然后以整生的爱
点燃一盏灯
我是火
随时可能熄灭
因为风的缘故
蟹爪花
或许你并不因此而就悲哀吧
蟹爪花沿着瓦盆四周一一爆燃
且在静寂中一齐回过头来
你打着手势在窗口,在深红的绝望里
在青色筋络的纠结中你开始说:裸
便有体香溢出
一瓣
吐
再一瓣
蟹爪花
横着
占有你额上全部的天空
在最美的时刻你开始说:痛
枝叶舒放,茎中水声盈耳
你顿然怔住
在花朵绽裂一如伤口的时刻
你才辨识自己
余光中:难得的妙才
年轻时,读余光中,很感动,比如他的《乡愁四韵》,他的《白玉苦瓜》。他的诗,可算是抒写“大我”的诗,是国家、民族、文化的一种认知与情感,却还是写得情深意切,很有感染力,甚至让你不能抑止,让你不再冷静地要跟着他去爱、去恨,去爱那样一种“大我”,也就是去表达“大我的爱”,却又不會觉得是否太矫情、太空乏普泛了。
后来,听说诗人回福建永春老家,没有机会陪着下去,但听陪伴下去的诗人说,余老前辈跪向家乡的土地,那种真情流露,和他的诗一样,非常感动人。性情使然,固而感人,抒“小我之情”如此,抒“大我之情”亦如此。
不过,这次编《中国当代诗人禅意诗选读》时,更多地还是选他“较为冷调的诗”来读,也就选取他那些“抒小我之情的诗”来读,不是怕再被那样“大我”“大爱”情怀感动,不是怕还是那样跟着为“大我”激情澎湃。而是他这一类诗更有利于我们厘清诗意与禅意,更贴近每个人的生活,更易于抚在每个人软软的心上。他“冷调”的诗,很唯美,很诚挚,也很思辨,富禅意。
灵感,是诗人、艺术家最为崇尚的美好东西,却是那样飘忽,难于捉摸,要用文字准确地表达是具有很高难度的。余光中先生通过具象手法、清晰地描绘出“灵感”的特质,又鲜明地表现了其不可捉摸性。仅从《灵感》这一首小诗,足可见其大家风范,难得的“妙才”!
附:余光中的诗(五首)
余光中(1928—2017),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10月生于江苏南京,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 1953年,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