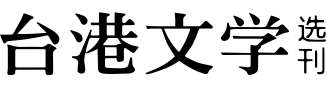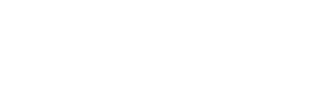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裁的书,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们,记述老师孔子当时向弟子们的教学和解答问题等。粗读起来,好像条理层次不清,分类又不合系统。如果加以悉心体会,就会发现它的精神和体系自有条贯,并非次序紊乱,漫无目的。读书必要另具只眼,才不会瞎摸乱撞。儒家门墙在望,只要自有眼目,便可由此书中体会得孔门学问的宗旨与精神所在,不会轻易被人瞒过去了。
学问的基本
第一篇的《学而》,是孔门弟子汇编孔子所教为学的宗旨与目的,以及为学的精神和为学态度的基本道理,是全书二十篇的纲领,所以首先要深切体认。
子曰:學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通篇首先提出孔子教示为学的精神与态度,要弟子们应当为学问而学问,不是为功名利禄而学问。它的重心在于“时”字和“说(悦)”字。为什么呢?因为学问之道,在于造就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要如何立身处世的道理。至于知识和文学等,只是整个学问中的一部分,并非学问的最高目的。立身就是自立,处世就是立人,因此为学的精神,要做到随时随地,在事事物物上体认。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无一而非学问,遂使道理日渐透彻,兴趣日渐浓厚,由好之者而变为乐之者,才是学而“时”习之到达了“说(悦)”的程度。倘是只为求知识文学而学问,事实上有时反而觉得很苦,哪里还会悦得起来呢!只有在学问上随时有会于心者,才能心胸开豁,无往而不悦的。一定要有这种见解,才不会把这句话变成教条,才能领略到,这一句的确是为学的至理名言了。
因此他又跟着说,真正为学问的人,首先就要确立一种精神,认清人生的本分,然后能够以一生甘于淡泊、乐于寂寞的胸襟,方能顺时因势,随时偕行,如此才可以言“学”。儒者以学问为本,以持身谋生为务;谋生与职业,是持身的要务,不能与学问混为一谈。但要知道,“德不孤,必有邻”,只要学问真有成就,自然会如响斯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当然会有志同道合的良朋益友,互相过从,所以他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如果把这句话只解为朋友来便乐了,有时候是讲不通的。因为朋友不一定都是令人乐的,有良朋也有害友,坏朋友来了的时候,你纵使硬把这句话贴在心里做教条,也会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之叹了。所谓远方,是说不一定是目前亲近的朋友,千里趋风,知音在迩,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他跟着又说: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那是进一步又告诉你,为学问是为了自学做人,目的并不在求人知,假定寂寞一生,默默无闻,没有半个知己,也不要怨天尤人才对。“愠”,是内心怨愤;“君子”,是儒者学问成就者的美称。通常的人情,总是喜欢自我表扬,都有自视甚高的心理,所以无真学问者,便有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甚至对社会人群,生起一种仇恨怨怼的心理。因此在《里仁》篇中,孔子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了。这个立,就是要建立学问的宗旨与中心,如要真为学问,首先就要确定这个精神和态度,然后才可以谈学问。这三则记载,就是标出孔门为学的精神和态度,首尾条贯井然,并非如教条一样,各自分立的。
循此一贯的线索,便可以得到其中的旨趣了。
孔门为学的精神与态度,既已了解,那么,为学又学个什么呢?于是便引出孔门弟子有若的一则话来了。
孝弟是什么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名有若,鲁人,是孔子的弟子,少孔子四十三岁。他指出孔子教示为学问的目的,是在完成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也可以说是完成一个真人,就是以孝与弟,作为学问的基本。为什么呢?“孝”是为人儿女者,上对父母的一种真性情的表现,也就是天性至爱的升华,这是一个为学的纵向中心,所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贯串上下的。“弟”是指对兄弟姊妹,乃至朋友社会人群真诚的友爱,这是为学的横向中心,所谓由亲亲、仁民,而至于爱物。弟也就是友弟,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友爱的基础。
人为什么一定要孝弟呢?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他不同于动物之处,就是有灵性和感情。孝与弟,是人们性情中最亲切的爱之表现,一个人对父母兄弟姊妹骨肉之间,如果没有真性情和真感情,这就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们都是做过儿女的,也都有机会要做父母,至于兄弟姊妹朋友,大家也都是有过经验的,试想,假使对上下左右,没有孝弟的至性至情,那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形态呢?所以,以孝弟为学问的基本,就是要求人人培养这种真性情的美德。由此扩而充之,对社会国家和人类,才有真爱。
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是由于这个道理而来。西方的文化,大体很注重社会人群横的一面,所以由男女夫妇的爱,扩而充之,就是社会和国家爱的观念,而且重视下面较多;至于对上面的父母呢,并不特别注重孝道,只是下对儿女的养育,尽了最大的爱,儿女长大了,上对父母也就不一定要尽孝。再看西方的上,是以形而上做对象,建立一个神,作为信仰的皈依,也许忽略了人与神之间基本的桥梁——对父母的孝道。所以举世重视的西方文化,好像只背了一个丁字架在世界上走,似乎不能撑持这个上下左右十方的天地了。
由此可以认识孔子教学的伟大处,真是放之六合而皆准,弥纶天地而不过。所以有子在这里,告诉你孔门教人为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性中的真性情。它的基本,就是先要做到孝与弟。如果人生最基本的孝弟真情都没有了,还谈得到其他吗?因此他再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不孝弟,必定会犯上,那是必然的趋势和结果,那是人性的反面,也是缺乏良好教养的表现。古文鲜字与少字通用,毋须另讲。
为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性最基本的孝弟,为什么在这里,又单独地插入一则说“仁”的话呢?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则话在这里插入《学而》篇里,未免显得太突兀了。其实并不奇特,“仁”之一字,是我们传统文化里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学问,以完成一个人达到仁的境界为宗旨。上面把孔门为学的精神、态度与目的,都已提出来了,到此才显示为学的宗旨,在于完成一个“仁”字。学不至仁,便无成就。然而仁不在于学理上的巧言思辨和外表的做作,所以在《卫灵公》篇及《阳货》篇中,又引孔子的话来证明说:
“巧言乱德”,“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仁是性情心性的最高境界,有体有用,必须要笃实履践才能做到。第四《里仁》篇中,专讲此道,所以不必在这里多做讨论。这里单独插入这一则,只为显出为学的宗旨,乃顺承上面所讲各则而来,是一画龙点睛之笔。如果你认为“巧言”只是指巧辩之言,“令色”只是指阿谀的态度,那么除了不巧言、不令色以外,便算是达到仁的境界了吗?这未免太不踏实。要知道,为学而达到仁的境界的人,在孔子生平,是绝少轻许的,就如继传孔门道统的曾参,也自谦地不敢轻易言仁。所以在提出为学宗旨的“仁”字以后,加入了曾参的一则话,表示学而至仁,他亦有所不敢造次轻言之慨。但他说自己只能做到日日以三事反省自己,也许略近于仁吧!
你每天反省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待人接物,“无一事而不尽心谓之忠”。立身处世,“无一物而不尽情谓之信”。《学而》一篇,以“孝”“弟”“忠”“信”四个字为学问的准则。孝弟是内以持己,忠信是外以致用,内外备至,体用兼圆,这是孔门教学完成仁的境界的极则。所以在这里,曾子只提出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的两件事,日日以此省察自己的笃实履践功夫,希望不辜负夫子的谆谆传授,那才是学问的用力重点。所谓“传不习乎”,就是指夫子的所传所教,自己日日反省实践的功夫,是否真能做到了呢?
由此可见孔门当时为学的风气,师弟之间,兢兢业业,孜孜以学问为务的精神,是如此地诚敬亲切,踏实履践。如果只把它作为教诫式的教条来看,有时候就会看成虚文了。由于这三句话,再反观体察今日的社会人群,无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大家相处,到处都是“当面春风背后雪”,而坚持德行尽忠尽信者少,玩弄权术而不忠不信者多。大家都感觉世风愈来愈坏,只是无法可以挽回,正因为失去了儒家所教的做人的学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