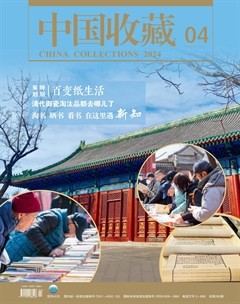1 0 6 4 年,蔡襄挥毫写下了《大研帖》。落款有“闰月”“廿一日”字样。核对史料,当年五月为闰月,故蔡襄写此札的时间进一步明确了。此时,距蔡襄去世还有三年时间。
《大研帖》内容不长:
襄启。大研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花盆亦佳品,感荷厚意。以珪易邽,若用商于六里则可,真则赵璧难舍。尚未决之,更须面议也。襄上,彦猷足下。廿一日,甲辰闰月。
好友唐询要跟蔡襄换墨,于是蔡襄写了这封回信,后世称为《大研帖》。苏轼手札曾被戏称为“换羊书”,此札可呼为“换墨帖”。由《大研帖》也会想到米芾的《紫金研帖》,都是关于砚台的。米和蔡两人虽然性情差异看似极大,但必定有投缘之处,才可能同列“宋四家”。简单地说,就是共通的文人天性。
换墨却得一札
唐询(10 0 5年至10 6 4年),字彦猷,传为帝尧后裔。《大研帖》最后有“彦猷足下”字眼,故此帖又名《致彦猷尺牍》,10 61年蔡襄还写过《远蒙帖》,又名《彦猷侍读帖》,可见按两人交往频繁。从唐询的生卒年来看,在收到《大研帖》当年去世,故算得上两人之间的“绝唱”。蔡襄撰有《唐彦猷挽词》,其中写道:“骾亮驰名久,孤高进路难。富文平日业,劝学晚年官。隧外春江静,林边晓露漙。唯应坟上土,犹解是芝兰。”唐氏好书法,尝得欧阳询书数行行书真迹,精思学之,其名亦有一“询”字,推想与此相关。
唐询比蔡襄年长8岁,没有参加科考,但富有才学。其为世人所知者并非政绩,也非书法,而是对砚台的收藏和研究,最终辑成《砚录》(已佚)。唐询性格孤傲清高,交往的人不多,蔡襄是为数极少的亲密朋友之一。彼此的交往,砚是重要纽带。蔡襄50岁以后,有一段时间曾与唐询同在汴京共事。从《大研帖》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文人天性“好(hào)玩”也“好(hǎo)玩”的一面:前者意味着嗜砚成癖,无癖不交;后者则是要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天性不灭,天性永存,就会有好的创作状态,就会有佳作问世。对比当下的诸多创作,技法高低不论,关键是没有了人情味,只能說面目可憎。
话说某次,蔡襄参加宋仁宗的私人宴会,皇帝赐了一锭老墨给他。蔡襄仔细观摩后发现,与平时所见的李廷珪墨似曾相识,但又不完全一样。经过深入研究,认定御赐墨块是李廷珪的父亲李超所制。父子俩的区别在于,父亲用的是“邽”,儿子用的是“珪”。唐询是好墨之人,听闻有此等宝物,于是就选了一方大砚台、一个茶台和一块李廷珪墨,用来置换蔡襄的“李廷邽墨”。于是蔡襄就回了一封信,即《大研帖》。其开篇即言“大研盈尺”,要知道,常见的砚台一般规格才20多厘米,“大研”就是大规格的砚台,“盈尺”就是一尺多。北宋时期的一尺,约合现在的31厘米,这样的砚台很少见。
在信中,蔡襄先是大大夸赞了老朋友送来的大砚台和茶台,赏心悦目、蓬荜生辉,所谓“ 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斋”即书房,“ 繇”通“尤”,表示特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