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肺结核病中离开了世界。
100年后,这位希望自己不要继续被阅读的作家,却仍然被我们阅读着。
值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之际,中信出版社·春潮Nov+出版了《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联合青年学者曾意进行翻译。
卡夫卡书写20世纪的悖谬,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悖论。“死去元知万事空”,卡夫卡生前留下遗嘱希望遗稿全数焚毁,但他不仅作为作家继续被人阅读了100年,而且影响了这100年来的文学、哲学、法学、神学、政治学研究。短暂的一生里,面对着20世纪的权力与崩塌、荒诞与尴尬,卡夫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焦虑和惊恐中。他试图通过写作对这个世界发出他的警告,如今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如何准确地预言了我们的時代。
“卡夫卡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特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21世纪,我们要怎样解读卡夫卡?
以下是南风窗与曾艳兵教授的对话。
画家卡夫卡
南风窗:为什么这次,我们选择从“作为画家的卡夫卡”这一面来接近卡夫卡?你是在什么时候、借助什么契机,开始研究作为画家的卡夫卡的?
曾艳兵:卡夫卡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早就被人熟知,但是作为一个画家,人们对他了解还不够。但我们知道卡夫卡是喜欢画的,我们在各种传记里都能看到,他练习画画,参加绘画的学习班和艺术沙龙,与艺术家往来。跟他的手稿一起,最后卡夫卡也留下了大量的画作。
我们知道,卡夫卡生前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保管了卡夫卡的遗稿,1968年布罗德去世后,他的秘书霍夫开始陆续出售部分遗产,这期间也有出版商找到霍夫,商议出版卡夫卡画作事宜,但霍夫的要价让出版商望而却步。因此,卡夫卡的画作始终秘不示人。2008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作为原告,要求获得卡夫卡文学遗产的所有权。于是,一场耗时将近10年的官司开始了,最终打到了以色列最高法院。2016年8月7日原告胜诉,这桩官司引起国际轰动。2019年7月15日,卡夫卡的手稿与画作从苏黎世被转移到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国家文化遗产”,卡夫卡的遗稿不再封存,对公众开放。卡夫卡遗产中最后一个未知部分终于可以公开了,这就是他的画作。
中信出版社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觉得有出版这些画作的必要,去年是卡夫卡诞辰140周年,今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在这个时机把卡夫卡的遗产继续介绍给中国读者,应当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南风窗:卡夫卡画作的风格和方法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画作与他的写作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曾艳兵: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7月3日,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欧洲的艺术热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特别是绘画艺术。绘画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现代主义这些思潮和流派首先都是从绘画过来的。现代性这个概念,追根溯源,其实来自波德莱尔对法国几个画家的评论,所以绘画和文学本身就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当时欧洲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印象派等等很多画派,包括东方的艺术,比如日本的版画,对卡夫卡产生了深刻影响。
卡夫卡着重关注的是绘画的非描述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术出现,当时的艺术家认为绘画作为一种艺术不能再满足于复制现实,而是要高于生活,特别是要反映人内心的真实,这是照相术难以呈现的。
卡夫卡的画跟他的写作有相似的地方。他的画线条简洁,风格奇特、怪异,跟他的写作风格是一致的。而且画和文字可以“互注”,就是互为阐释,卡夫卡在写作的时候,写着写着就会画上几笔,然后接着写。
卡夫卡的绘画里频繁出现弱者的姿态,其中的人物“根基”都不牢,总像是飘在半空中,还有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动作,朱迪斯·巴特勒也注意到这一点,认为这种绘画风格跟他对现实的看法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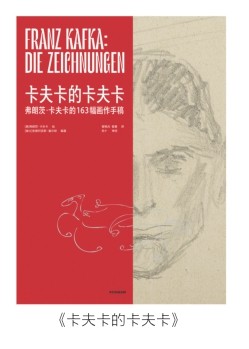
“小说这样写,有点意思了”
南风窗:你在过去的著述当中曾提及,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卡夫卡,在布鲁姆、阿伦特、阿甘本、本雅明、布莱希特的眼中,卡夫卡有不一样的形象和不一样的意义。为什么对卡夫卡的阐释会如此多样?你眼中的卡夫卡是什么样的?
曾艳兵: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对卡夫卡阐释的多样性,来源于他作品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寓言性。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卡夫卡的意义固定在某一个方面。而且,卡夫卡的很多小说都有“ 开放的结尾”,特别是长篇小说,都是没写完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去阐释,神学的、政治学的(比如阿伦特)、法哲学的(比如阿甘本)、心理学的,等等方面。我个人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文学家,一个书写生命哲学和人的存在意义的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