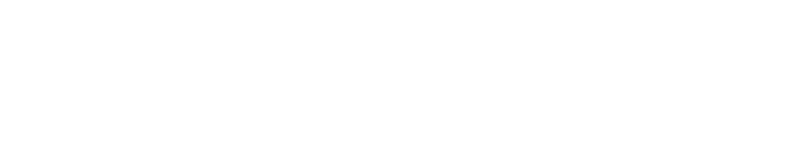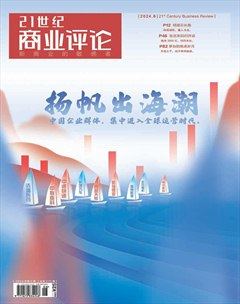很多年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茅台酒是一个传说。
在尼克松访华的新闻照片中,人们看到了茅台酒;在全国评酒会的榜单上,又看到茅台酒。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酒似乎并不存在,它与民间绝缘,只闻其名,难见其身。
作家叶辛是在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70年代末,他听人说茅台酒“很不得了”,就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当时,上海滩最时髦的地方,是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叶辛跑到南京路,从路头跑到路尾,逛遍了南京路上所有的百货商店,就是没有找到茅台酒。
茅台酒厂,看上去都顺风顺水,有一个苦恼一直缠绕不去:企业利润非常微薄。用任过厂长的邹开良的话说:“茅台酒是一个讨饭的王子。”
从建厂到20世纪70年代,茅台酒厂的销售实行统购包销,因执行国家高税、商业厚利、工厂薄利的计划政策,每调出一吨茅台酒,商业获利5000~6000元,工厂仅获利60元。
其后,茅台突然被推进市场的大海洋,走向普通大众,起初,它也一样呛水。
王子讨饭
茅台“王子讨饭”的原因,便是早期没有销售的权利。
从50年代合并建厂的第一天起,茅台酒的销售权就在专卖机构手上,酒厂仅仅作为一个内部结算的生产单元存在。
起初,茅台酒的出厂价(当年叫调拨价)采用一种纯计划性模式。
1958 年之前,其实行成本定价法,即工厂一年下来,把所有的生产和运营管理成本核算上报,专卖公司给一个留利比例。
利润率基本上为0.65%~1%,就是说,100 万元的生产收入,最多可以留1万元的利润,十分可怜,但总是有利润的。
1958年之后,改为收支两条线,即专卖公司定一个调拨价格,生产成本如何,它就不管了。很快,工厂就陷入常年的亏损。
酒厂与渠道之间的利益分配,一直就畸形得惊人,如酒厂历史资料所记录的,相差足足有100倍。
如1951年,专卖机构给酒厂的调拨价为每瓶 1.31元,而专卖零售价为2.25元;30年后的1981 年,调拨价为每瓶8.4元,专卖零售价为25元;到80年代中期,在华侨商店和友谊商店的外面,茅台酒的黑市价格被炒到140元,出厂价还是8.4元。
其后,全国进行国营企业“放权让利”试点改革。时任茅台厂长的周高廉,几次跑省里要求将茅台酒厂列入试点,没有被允许,理由是“茅台酒很特殊,而且酒类属于专卖事业,先放一放再说”。
到1980年,为了安抚酒厂,商业部门做出了让步,每吨酒给予1200元的补贴,到1983年又增加到7800元。
在那一时期,企业承包制改革如火如荼,国家体制改革部门以“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为原则,杏花村汾酒厂等酒企都享受到了这样的政策,拼命扩大产能,多酿的酒都是计划外的,可以自主销售。
而茅台酒厂因为外贸和外交的两重特殊性,成了改革的“例外”。上级部门宁可给定额的补贴,也不愿意给自主权。
酒厂终于获得一定的销售自由,还是因为一个特别人物的“帮忙”。
1985年,原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中将“重走长征路”到茅台酒厂,时任厂长的邹开良请他喝酒。喝到高兴处,副司令员问:“厂里现在有什么困难吗?”邹开良说:“缺钱,很缺钱,非常缺钱。”
副司令员的脸上就有些为难了。邹开良乘机请他向上级请个愿:“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东西,能不能要一定比例的产品销售权?”
周仁杰回去后,认真地帮酒厂办这件事情,报告一直打到国务院,到6月,轻工业部和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先后下文,允许茅台酒厂将超计划部分的30%,进行自主销售。
这份文件一下,当年酒厂实现利润576万元,比上一年翻一番还多。
当挤牙膏般地从计划体制中争取自主权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这只紧握的手,会在某一天突然完全打开。
1988年,中央政府推行物价改革,废除“价格双轨制”,宣布酒类价格全面放开,除了出口仍由中粮包销,国内市场允许自由竞争。
挣扎了整整37年的茅台酒厂,一直哭着喊着要自主销售,当自主销售到来时,其实并没有准备好。
唯一的自信是,咱们是“国家名酒”,没有人不知道。
跌到民间
当年,叶辛的问题是,去哪里买茅台酒,邹开良的困扰却是,去哪里卖茅台酒?酿了这么多年的茅台酒,酒厂上上下下,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喝茅台酒的人。
1986年,时任茅台总工程师的季克良,在北京开了第一家茅台酒专营店,之所以选在西苑饭店,因为它的周边有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建设部等主要部委,季克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茅台酒的主力消费者。
当自主销售到来时,2000多吨酒如何销售,酒厂是完全没有底的。
1989年,国家又进行经济调整,市场疲软,产销失衡,茅台酒被列为社会集体控购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