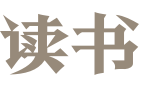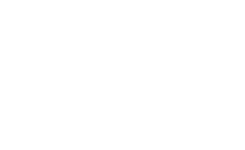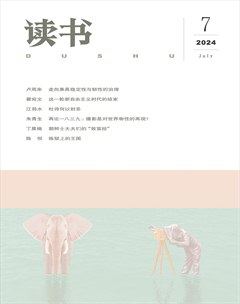杜甫是中国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世界上也找不出比他更大的抒情诗人了。他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作品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高,对后世的影响如此之深远,故一千多年来,其诗被称为“诗史”,其人被称为“诗圣”。一部《杜工部集》,是诗人的起居注、交游录,是地方的食货志、风俗通,是自然的草木谱、山水经,而尤其是大唐由盛转衰之际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事件的纪实。
杜甫一生的荣枯,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唐代那一重大历史转折期的缩影。因为他,国人对史上同样惨烈的永嘉之祸、黄巢之乱、靖康之难、甲申之变的记忆,都不如对安史之乱来得清晰与深刻。就像英国人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得到的罗马史知识超过普鲁塔克《名人传》,我们对安史之乱的了解,得之于杜诗的,也超过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正史所保存的是时间、数字等冷记忆,诗人却给出视听化的鲜活经验,带着体温、景深和饱满的颗粒感。卢卡奇在《论莎士比亚现实性的一个方面》一文中说:“在莎剧中,命运曲线的节奏从来都不仅仅是一条基本的、一般的直线,而是由许多丰富多彩的爆发性瞬间组成,这些瞬间似乎完全吸收进 hicet nunc(此时此地)了。”我们读着杜诗,看着九庙被焚时热浪灼飞出去的瓦、群胡腰间凝血的箭、女儿被捂住生怕她出声的嘴、幼子脏兮兮没穿袜子的脚、捉来当丁的肥男和瘦男、翻墙逃走的老翁、月光下的战地白骨……我们沉浸在诗人的当下,感其所感,思其所思,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化身为彼,移情于此。老杜“栖栖一代中”的书写,就这样笼罩百代,上升为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内化为我们各自的心理现实。按照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杜诗作为诗史,是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读杜诗,可以论其世,可以知其人。自有文字或文学以来,从未有一个人被如此真切而充分地写过。尤其是四十岁之后的二十年,杜甫经过的每段日子,其一言一行,一悲一喜,不止履历,甚至病历,都历历可辨。我们不但掌握他外在的行踪,还能透视他内在的心迹。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心系廊庙,又情牵山林。儒行世间,而道求方外。既恤民瘼,亦体时艰。虽感主恩,还规君过。说他疏狂,他又谨慎。说他严肃,他却幽默。说他迂直,他也圆通。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然而初心不忘,痴性不改。因此,说到底,这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对君上忠,对朋友诚,对妻子爱,对儿女宠,对兄弟厚,对乡邻亲,而又好健马,敬义鹘,怜池鹅,惜溪鱼,有万物一体之仁。张戒《岁寒堂诗话》曰:“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可老杜不仅是我们情感教育的教父,影响了无数人的价值观,还引导了我们观物与审美的眼光,令我们看山不再是原初的山,看水不再是本来的水。举凡陇阪、蜀道、锦江、夔门、湘水,杜诗都给勾了线,着了色。更有甚者,我们看马会想到房兵曹的马,看鹰会想到王兵马使的鹰,甚至连看花也不纯粹是自然的花,因为有《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与《绝句漫兴九首》,宋元明清的诗人,为花颠狂为花恼,替花惋惜替花愁,一下笔就滑向了老杜的文字配方。
总之,杜甫以他的写作再现了自身的时代,又参与重塑了后人对于各自时代的感知与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杜诗总是与后来的时代形成互文,为后起的生命做出代言。诗人在其诗中融入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又被后人一代又一代汇入自身的经验,不断拿自己的世界与杜甫的世界相互参照,彼此确认,从而使其意义不断增殖,而且永无休止,正所谓“其诗日读而愈新,其义日出而无尽”也。
杜甫被称为诗圣。“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抱朴子·辨问》)这样说来,杜甫也就是最会写诗,或者说,诗写得最好的人。那么,为什么好?怎么样好?以下就围绕着风格、结构、节奏三方面,贯穿起句法、章法、韵法等要点,加以阐说。
一部杜诗,地负海涵,千汇万状。元稹《墓系铭》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叶燮赞其“包源流,综正变”,无非在说:向前看,《詩经》的典雅、《楚辞》的藻艳、建安的慷慨、齐梁的绮靡,杜甫学什么像什么;向后看,昌黎的奇险、香山的平易、长吉的幽仄、义山的精深,杜甫要什么有什么。这正是韩愈所谓“独有工部称全美”,王禹偁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
杜诗穷极变化,却有一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导风格,这就是沉郁顿挫。语出杜甫《进雕赋表》:“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本来是说扬雄、枚皋文思有迟速之别,而老杜自谓能兼之,快也快得,慢也慢得。慢起来的话,思则深沉,辞亦顿挫;快起来的话,时虽短促,才却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