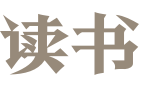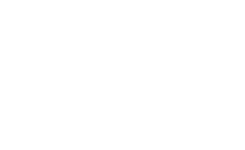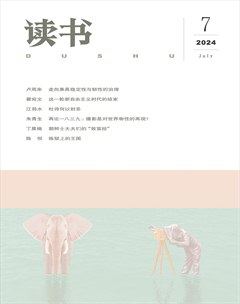一
二0二三年秋天,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讲座教授梅祖麟先生逝世,从此欧美汉学与中国语言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痛失一位良友。
梅祖麟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武进。父亲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伯父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一九四六年春,燕京大学结束了成都办学时期,迁回当时的北平。这年十月,梅贻宝几经周折,完成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作为高中生的梅祖麟,第一次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时任燕大语言学教授高名凯先生的名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燕大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阵容强大,陆志韦、俞敏、林焘、陈梦家、吴文祺等,皆在该校开课。而对于梅先生近七十年学术生涯的研究旨趣而言,高名凯无疑是对其启发最大的前辈学者之一。
高名凯于一九三一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旋即攻读本校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业师陆志韦先生的感召与鼓励之下,高氏转向中国语言学领域。一九三七年九月,高氏受母校燕大委派,远赴法国巴黎,从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攻读博士学位,并完成了题为《汉语介词之真价值》(一九四0)的学位论文。这一“哲学气味甚浓”的理论性著作,与稍后问世的《汉语规定词“的”》(一九四四)、《汉语句终词的研究》(一九四六)、《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一九四八)、《汉语语法论》(一九四八)等,开创了汉语近代语法史研究的新风气。诚如梅祖麟所言,该领域的学者可分作三个流派,马伯乐、高名凯、戴密微(P. Demieville)为巴黎学派,入矢义高、太田辰夫、柳田圣山、志村良治等可谓京都学派,胡适、王力、吕叔湘则为中国本土的近代语法史名家。
一九四九年春,梅祖麟在上海圣约翰中学高中学业。当年五月,随父母乘坐“戈登将军号”轮船赴美。一九五四年,获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也是梅贻宝先生的母校)数学学士学位,并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和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四十年后,在回顾学术历程时,梅先生说自己“四十五岁以前是玩学问,四十五岁以后才打定主意做学问”,这是因为“虽然在哲学、文学、语言学三方面都发表过几篇文章,但是好的是跟罗杰瑞(J . Norman)、高友工合写的,文章里好的意见是他们的,自己的平平而已”(《我的学思历程》,载《中国语文研究》二00一年第一期,6 页)。这当然是梅先生的一种自谦的说法,比较客观的评价,是梅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曾先后致力于语言哲学(博士论文及其延续)、中古聲律与律诗及其来源、汉藏语比较诸领域的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乔姆斯基(N. Chomsky)的《句法结构》(荷兰海牙,一九五七年英文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诞生,不再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只强调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而提倡对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及其规律做出解释。但是事实远比理论丰富,充分描写永远是合理解释的前提。梅祖麟坦言:“那一阵子乔姆斯基和麻省理工学派的语法理论变动很快,过三五年就有一套新理论出现,我渐渐觉得跟着人家跑有疲于奔命之感。……久而久之,这种困惑让我走到汉语语言史的领域来。”与梅先生同时代、曾一度追随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家,如余霭芹、王士元、马提索夫(J . Mat i sof f)、拉波夫(W. Labov)等,后来也都不约而同地开辟了新的学术道路。即便如此,梅先生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书目季刊》一九八0年第二期)一文中,仍然实事求是地指出,形式语法的研究理念对于汉语历史的研究是具有启发作用的,“生成语法论(generative grammar)兴起之后,我们不但要描写某一时期语法的表层结构,而又要进一步探求其深层结构,这种表层结构往往和更早一期语言的表层结构关连”,表现出了做学问应有的饮水思源之心。
梅祖麟于一九五四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学位,差不多时间入读该校的还有高友工、张光直、余英时、吴大钧、杨振平几位,以及从台湾大学赴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访问学人、汉语音韵学名家董同龢先生。
高友工和梅祖麟在谈到各自师承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早年的授业恩师董同龢。高氏将董先生视为“最尊敬的老师”“对我最宽容、最了解的前辈”。高氏说:“对我转入中文系影响最大的是在台大的董同龢老师。……他对我们这些大一学生,完全当作是他的同辈人对待,上课时鼓励学生发问、论辩,也因此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美典·自序》,19页)梅氏则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一文中说:“考订整理基本资料是董先生对音韵史的贡献之一,早年《〈切韵指章图〉中的几个问题》纠正了高本汉的错误。到台湾后又领导全盘整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