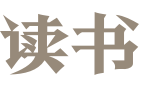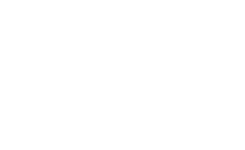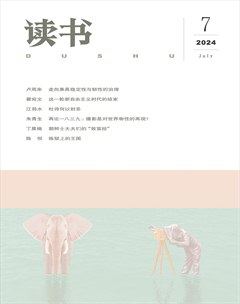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现代建筑巨擘勒·柯布西耶(Le Corbus ier)在其宣言书式著作《走向新建筑》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逐出了真正的宫殿,他的小朝廷被迫从明清两朝营建数百年的紫禁城后半部分中迁出。早在十二年前,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紫禁城前半部,包括三大殿的主体部分,就成为博物馆性质的古物陈列所,开放给公众参观游览。宫殿作为帝制时代皇权象征的意义被抛弃,但其所从属的中国建筑传统正在被重估和转化。在此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推力,来自外国来华建筑师和建筑史研究者。其中,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建筑师亨利·茂飞(Henry K. Murphy)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
一九一四年,时年三十七岁,对中国建筑传统所知甚少的茂飞远赴中国开展新业务,他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接受源自巴黎美术学院的“布扎”(Beaux-Arts)体系训练。此后的二十余年里,茂飞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作品遍布中国南北各地,这些结合中国明清官式建筑的部分特征(屋顶、以新材料仿制的柱子及装饰)和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平面布局以及近代建筑技术的“适应性建筑”,成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中著名大学校园中那些“大屋顶”建筑,尤其引人注目,不少至今仍作为地标屹立。尽管如此,当建筑史学者郭伟杰(Jeffrey W.Cody)开展研究之时,茂飞在西方已经基本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他一直游离于建筑学界的研究视野之外,几乎完全被建筑史学家和民国史学家所忽视。”另一方面,茂飞所开创的传统,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建筑师,同时在建筑师和评论者那里引起争论。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茂飞的实践和观念也在建筑史和思想史意义上被多重解读,其中不乏误解。透过郭伟杰这本完成于二十多年前的著作《筑业中国:一九一四——一九三五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我们得以一窥茂飞的生平及其作品所处的历史脉络,进而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上思想与物质的互动、传统在遭受冲击之后如何被重新发明,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思想、知识和技术的交错环流和互动。
一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作为整体的“传统”已经不复存在,王汎森认为:“由于思想分子之间原有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这些散开的分子只是材料, 形式已经不存在,新的理念或主义的介入,使它们不断游离并重组。”思想史上的抽象变化,通过建筑变得具有“及物性”,就如李士桥所言:“建筑既是思想的产物,也是创造思想的手段。”赖德霖认为,郭伟杰在《筑业中国》中试图回答“传统对于茂飞意味着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一种建筑传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在茂飞等人的建筑中,中国古建筑的若干特征被拆解下来,运用于新型的公共建筑设计之上。这些建筑师,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理解不尽相同,其思想主张,更有所差别。就茂飞而言,“中国建筑传统包含三个层面:以明清紫禁城(约一四二一至一八九四年 )为代表的体系性空間营造;适应上述宫殿式建筑和其他建筑类型(如宝塔等)的建筑形式语言;以及在斗栱交接、屋面处理及彩画配置等形式语言背后所蕴藏的结构或装饰性特征”(4—5 页)。他“试图将中国建筑从沉睡中唤醒,将其分解为独立的形式部件,去解决新的实际问题”。因而,茂飞并不是要亦步亦趋复制中国固有的建筑,而是要“解决新的实际问题,譬如怎样去规划教会的学校,以及如何运用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如钢梁和钢筋混凝土)”。
茂飞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位于距离北京一千五百公里的湖南长沙,是为雅礼协会创办的医院和学校营建新的校园和房屋。长沙当地的旧有建筑风格与北京宫殿的明清北方官式建筑颇有差异,但茂飞在结合甲方要求采用中国样式的时候,却没有选择本地风格,他保留了醒目的“大屋顶”(庑殿顶或者歇山顶),但放弃了陡峭的飞檐、繁复的本地化装饰等内容。茂飞更青睐紫禁城中的宫殿式建筑,而非多样的本地传统。跟茂飞同时或稍早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已经有过结合本地建筑特征进行设计的经验。一八九四年由通和洋行设计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便模仿了具有陡峭飞檐的江南风格屋顶,将之置于一座殖民地外廊式砖石洋楼之上;英国建筑师荣杜易(Rownt ree),在设计位于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建筑时,更多地使用了四川当地建筑风格的装饰元素和建材(使用青砖作为外墙材料而非红砖,使用当地所产的瓦片覆盖屋顶),配合西方“贵格大学”风格的山形立面和平面以及西式的建筑基础和桁架结构。茂飞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阅读文献和参观北京等地的古建筑,对中国建筑传统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决定在实践中体现自己对中国建筑的理解和品位。
彭长歆指出,茂飞对北方官式建筑的借鉴“规范了当时‘中国风格’的多元解释”,因此为民族主义者“表达正统中国和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建筑形式提供了方法论”。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建筑风格的地域多样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为何被边缘化甚至摒弃?
对建筑物风格的重视乃至将其视为民族国家象征、建筑师在近现代中国地位的提升,本身也是一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