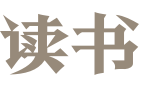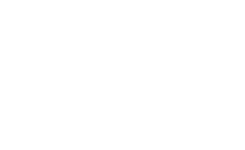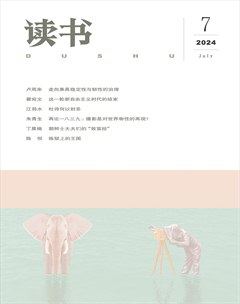一、聆音辨理
搞音乐的个个身怀绝技,能吵能闹,然而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呼啦啦拥进剧场,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家伙,四处扫视一圈剧场外观,脱下外装,拿起乐器,调律试音,感受音效。在指挥带领下,翻开乐谱,将曲目掐头去尾溜一遍。随后,让满台横倒竖歪的乐器盒,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打扫战场的士兵。临近演出,更衣换鞋,略施淡妆,独奏女演员不停忽闪着涂过润膏的长睫毛,男乐师则穿上熨好的白衬衫和黑制服,等待上场。
这是我坐在比利时与荷兰接壤的“荷赛特文化中心”观察乐师抵达音乐厅至开场间的过程。音乐家观察音乐家,能看到乱中有序,看到集体意志约束个体行为的潜文本——那叠放在指挥台上的总谱发出的社会学指令。一般人对音乐家的印象大致是松松垮垮,其实他们是一群纪律严明的人。纪律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支配每个声部的发声、起落、行止的文本——总谱。横律竖节,并轨而弹。差一拍你就进不去,多一拍你就冒出来;高半律你就刺耳,低半音你就讨人嫌。人们或许不奢望一大堆感性的人能够坐下来默契合作,认为那些头发总是比一般人长的音乐家像其乱发一样不可收拾,其实,一旦进入合奏,他们个性收敛,照章办事。培养规矩的方式,各行各业,自有套路。音乐是感性的,但乐队却是理性的。乐团培养人的基调,是步调一致。这个本本,就是总谱。亚当·斯密说:“个体的目标要符合群体的利益。”总谱就是“个体服从集体”的章程。崇尚精致协和的音乐家懂得,令人陶醉的享受,必须以精密配合和精确到位为前提。顾全大局,守律合辙。这是乐团的“家训”,这个家训,写在总谱上。
二、录音纪律
一九七三年,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吕剧小戏《半片天》的拍摄。那时的录音设备要一次性完成,任何人出错,全班人马都得重来。不像现在,多轨并行,定下节拍,分头录音,最后合成。当年的录音设备,意味着不能犯错。折磨人的滋味是当代音乐家体会不到的。小号、单簧管等容易“冒泡”的乐器,一旦出错,前功尽弃。整个乐队费了半天劲,疲劳耐力都达到了极限,谁若“冒泡”,埋怨、愤怒、咆哮,可不是一星半点。老乐手更是不客气, 得人抬不起头来。记得一次,一段乐曲几乎快录完了,小号手突然吹破了音,吹双簧管的老乐手,毫不客气地大声怒斥:“你别让我们陪着你瞎耽误工夫,出去练去。”当众羞辱,让小号手整天紧张兮兮。一个错音,重来一遍,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那是拿身体当儿戏。技术不是艺术要求,是生存要求。
主要唱段,演员要一气呵成,不能有半点纰漏。唱错一个字,拖错一段腔,大家怒目。录音棚不比舞台,错个字可以蒙混过关,上方吊着麦克风(那时),一个字不能错。导演要求一句一句来,全剧组人坐在旁边,众目睽睽,当众出丑,遭人奚落。真是难为人。“录音”红灯一亮,屏声敛气,蹑手蹑脚,唯恐犯错。运气好时,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乐队也情绪饱满,从头到尾谁也没出错,那是求之不得的天作之合。乐手们开玩笑“今晚是洞房花烛夜呀”。所以,个把小时的戏,在长春待了整整十一个月才完成。
卡拉扬指挥下柏林交响乐团建威立业的记录,包括大量乐手与指挥间博弈的情节。裹着资本运营、政治较量、权力争衡的事件,触目惊心。唯其如此,乐团才能获得秩序。《卡拉扬传记》与各类乐评,既塑造了意志坚定、手势精准、逻辑严谨的指挥家在与乐团冲突、博弈、制衡和公然无视性别禁忌等事件中一意孤行的个性,也塑造了一群与他一样有着超级天赋的音乐家对音乐、对艺术、对管理的不凡表述。让这群音乐家保持对指挥的崇拜,自然不是舞台上的花架子,还有排练中听辨隐伏声部错误的辨别力(常人难以企及的听辨力),以及更重要的,协调声部音响均衡的艺术判断力和协调人事关系的行政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