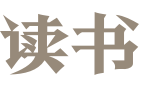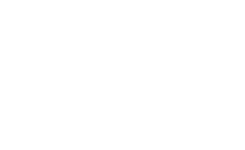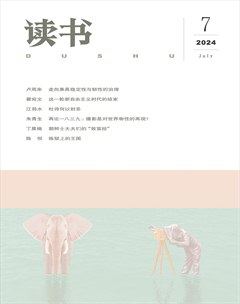旧约中《出埃及记》一卷,讲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法老的压迫、奔向上帝所许诺的乐土。摩西担负起争取自由的使命,成为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和法老展开一系列的缠斗,而所有這些情节的背后,都是上帝在筹划和安排。随后,以色列人逃至红海岸边,埃及追兵已至,自由的希望即将破灭,奴隶即将再次戴上枷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以色列的上帝出手,分开海水,让逃亡者从海底的干地走过。
在早期教会和中世纪的解经传统中,《出埃及记》一卷主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理解。解经家努力挖掘的,是此卷字面义之下暗藏的宗教象征含义。比如,以色列人过红海一事,被解释为预示基督教兴起之后的洗礼仪式,因为穿过海水就如同被洗濯了一番。又比如,摩西被解释为预示基督的降临。当摩西高举手中的杖(14:26-27),就如同以自己的身体摆出一个十字架形状的造型。基督教解经传统的主流,并未强调此卷中(在后代看来)很明显的反抗压迫、逃离暴政、争取自由的政治主题。但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出埃及记》的革命主题被挖掘出来,并且与《圣经》中其他一些相关段落,被不同时代的“革命者”反复解读、反复运用,最终在英美历史上形成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铸造出一套事关“自由”和“解放”的强大的政治话语。
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考菲(John Coffey)在《〈出埃及记〉与解放》(Exodus and Liberation )一书中,首次系统勾勒了这一套政治话语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轮廓。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约翰·加尔文到马丁·路德·金的解救政治》,足见此政治传统绵延之久。作者认为,从加尔文开始,英国革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废奴运动、美国内战、二十世纪民权运动,一直到二00八年奥巴马当选,都贯穿着一个神意强力干预历史的解救传统,作者称其为“解救政治”或者“救赎政治”(deliverance politics)。在大约四百五十年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在几乎所有历史危机时刻,都有大批知识精英和民众秉持这种政治信念,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同情和支持一切被压迫者,而且会在最后时刻主动援救,帮助被欺压的边缘群体最终战胜人间一切的压迫者。
“解救政治”的主要《圣经》依据是以下几段经文(我将最具标语特色的句子用黑体标出)。《利未记》中有关于“禧年”(Jubilee)的记载。根据这一制度设计,以色列人每耕种六年之后,第七年为“安息年”,彻底休耕。七个安息年之后,也就是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设为“禧年”,要让所有沦为债务奴隶的本族人获自由:“第五十年你们要当禧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25:10)。在后世的废奴运动中,这段话被广泛引用,被当作上帝明令要释放奴隶的证明。另外两句常被引用的经文,一句来自《以赛亚书》:“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58:6);另一句来自《路加福音》第四章所引用的《以赛亚书》:“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解放,被囚的出监牢”(61:1)。但所有这些旨在为穷苦人伸张正义的表达,都不如《出埃及记》的故事具体、生动,因为《出埃及记》前十五章是一篇连贯的叙事,记述了摩西带领人民逃离暴政、获得自由的全过程,因此构成此种“解救政治”最关键的《圣经》依据。
《圣经》中的一些语汇原本来自古代社会生活,比如“赎买”就让人想到古代奴隶市场的贩卖和释放。这些词语在后来基督教的解经传统中,被赋予神学含义,指的是将人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但是后世历史中最终会出现合适的时机,这些词语原生的社会政治语境又会被唤起,神学含义会随之隐退,词语的理解趋于字面化、具体化、政治化。“赎买”“救赎”“自由”这些词语开始直接对应于现实社会的关切,人们可以用《圣经》词语来描述人类现实。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事件,由于被《圣经》预言和《圣经》修辞来表述,也就同时带有《圣经》意义和神学规模,历史事件也就相应变成《圣经》事件,变成具有宗教意味的拯救事业(10 页)。这就形成一种双向运动。后世以《圣经》故事为先例、典范、样本,以《圣经》语汇来描述当下现实,以《圣经》观念来理解当下,打通《圣经》之“古”与当下之“今”。与此同时,当下也就被理解为《圣经》原型和典范在人类历史上最新的显现,当下也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为例,对于当时人来说,英国内战不仅是古典意义上的民族解放之战,更是《圣经》意义上的拯救之战。从一六四一年开始,“拯救”(del iverance)一词反复出现在各种书籍和小册子标题中,查理一世被比作埃及法老,而克伦威尔被称作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