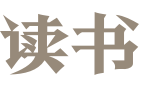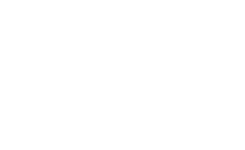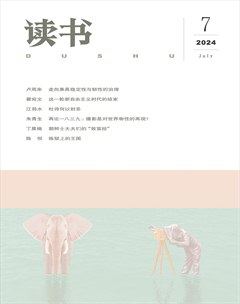在晚清官场,送礼是人际交往中的常态。当时有人作《一剪梅》一首,如此讽刺这种风气:“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京信,也就是外官写给京官的信函。由于外官需要打探京城的各种政治情报,囊中又有比较丰厚的灰色收入,定期写信笼络京官并送礼,早已形成不成文的惯例。炭敬,字面上即冬季买炭的“取暖费”,是当时最常见的送礼名目。各种笔记小说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不过,若要细究哪些官员送过或收过礼,礼的轻重如何,又不容易找到扎实的证据。毕竟,这种行为在当时虽然不算违法,但也上不了台面,相关材料很难完整保存下来。茅海建、白谦慎曾根据信函、电报与账簿分析张之洞、陈夔龙、吴大澂三位晚清名臣担任封疆大吏时的送礼情况,是罕有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茅海建:《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载《中华文史论丛》二0一二年第一期;《直隶总督陈夔龙宣统元年(1909)“炭敬”册》,载《中华文史论丛》二0二二年第二期。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231—243 页)。
那么,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史料可以反映收礼一方的情况吗?答案是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李鸿藻档案》(以下简称《李档》)十五函,装裱保存了上千通信札,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李鸿藻所收来信,其中“京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李鸿藻在光绪朝历任工、兵、吏、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久居政治中枢,又是理学大师、清流领袖,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外官巴结京官,自然不会忘记这位资望隆重的“高阳相国”。
给李鸿藻送礼的官员,上有督抚大员,下至七品知县,名义大多是前面提到的“炭敬”(因为在过年前馈赠,又称“年敬”)。官员们送炭敬的同时,一般都会附上一份贺年信。有的信中也会说点公事私事,但往往纯粹是一些吉祥而空洞的套话,犹如今日逢年过节时的群发短信,谁也不会仔细去看。如李鸿藻门生汪鸣銮的这通信函:
敬启者:于役天涯,光依北斗。宜春日下,瑞蔼东郊。敬惟宫保中堂夫子泰始凝厘,履端肇庆。金堤奉使,采风陈万福之歌;黄阁登庸,湛露荷九天之眷。台衡引领,轩舞倾心。鸣銮忝奉简书,瞬更节序。驾星轺而逾岭,又赋莘征;听腊鼓之迎年,虔陈椒颂。专肃,敬贺岁厘,祗请钧安。受业汪鸣銮谨启。
敬呈咏梅百韵,伏乞哂鉴。
这种骈四俪六、洋洋洒洒的内容,几乎没什么有效的信息量,仅有“驾星轺而逾岭”一句,据此可以推测出写信时间应在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底。“星轺”是使者的车驾,代指钦差。当年五月汪鸣銮奉旨钦派广东学政,从京师前往岭南。至于最后的“敬呈咏梅百韵”,字面上是说呈送一首咏梅的百韵诗,其实是赠银一百两的雅称。耻言阿堵,毕竟是士大夫习气。《李档》中的这类隐语,大多以赠诗为名,如“附呈吟梅百韵”“附呈献岁诗二十四韵”“外呈消寒百咏”“谨呈椒颂五十韵”“谨赋辛盘双柏”等等。梅花诗、消寒诗是文人岁末吟咏的常见题目,自不必说;“椒颂”典出西晋女子陈氏献给皇帝的《椒花颂》,是新年的颂辞;“辛盘”则指古人“元旦造五辛盘”的习俗,即以盘盛五种辛辣蔬菜而食。无论名目如何,关键只在后面的数字(“双柏”即“双百”)。此外,山西布政使胡聘之颇具创意地用了“谨呈红炭二百斤”的表述,内行人自然不会当真以为他送的是“炭”。不过,也不乏有人直白地写下“炭敬某某两”。
外官送给李鸿藻的炭敬,一般在五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视送礼人官职的高低肥瘠以及双方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我在《李档》中见到数目最大的两笔炭敬,来自崇光与文珮这两位粤海关监督,金额都是一千两。粤海关监督是著名的肥缺,炭敬自然格外丰厚,尽管两人信中都“谦逊”地把自己的馈赠称作“不腆微忱”。相反,李鸿藻的门生赵舒翘曾在某次贺年信的最后写道,“外呈菲敬四十金,微薄不胜愧赧”,则是真的觉得四十两银的馈赠太过菲薄。为此,他自我解嘲地表示老师的期待在于为官清正,自己也不敢勉强多送,又说自己担任的凤阳府知府一职是个苦缺,而且今年收成不好,钱粮缓征,手头更不宽裕。但他保证这笔炭敬出自堂堂正正的养廉银,请老师放心收下。
向李鸿藻送礼的人也包括京官。由于京官基本没有养廉银,又不像外官可以刮地皮,收入普遍较低,送礼时自然大方不了。当时有某位翰林作诗形容众多“穷京官”的窘状:“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这里提到的“师门二两银”,指门生拜门以及此后每逢年节馈赠老师的礼金,即所谓“贽敬”,二两银子是能够送出手的基本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