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出土文献 战国 春秋史 《左传》 孟荀
根据战国时期诸子著述的话语方式,许多学者认为先秦诸子著述具有史论结合、讲史、说体乃至故事小说的特征。①战国诸子著作这一特征颇与当时社会的整体风尚密切相关,所谓“春秋时人好言诗,而战国时人则好论史”,②正是这一社会风气的展现,且与孟子所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相契合:言说春秋史事、传闻、故事成为诸子百家的爱好和风尚。③以当今出土的简帛文献与诸子著述来看,《左传》所呈现的春秋史文本己不是春秋史事的原初状态:④结合当代社会所见的出土文献,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左传》的史料来源判定为“春秋事语”类文本,⑤即诸如上博简、清华简、枣纸简等短章型春秋史文本为《左传》的成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文本支撑。
这些有关《左传》史料来源的辨析,为进一步探究《左传》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基点。因此,根据学界对《左传》史料来源的诸多分析,笔者将以上博简、清华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出土文献为重要参照,来考察《左传》于战国社会的成书时段。
一、“预言解证法”及其局限性
现当代学者徐中舒指出“《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其中的“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因此可以根据应验的预言判断《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根据不验的预言来判断下限;在此基础上,徐中舒根据“郑先卫亡”判断《左传》的成书不能早于公元前375年,又根据“郑先卫亡”判断卫国虽未绝祀,但“已有亡征”,且“卫国危亡已在旦夕”,这种形势应指向于公元前354年至公元前35 1年魏赵两国的对抗和结盟,而《左传》所记“毕万之后必大”也与此相应,于此《左传》成书于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51年。①其后,当代学界普遍以《左传》所记预言的是否应验来推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如杨伯峻根据顾炎武《日知录》“左氏不必尽信”条所列“不必尽验”的预言,认为顾炎武所列不验预言正好用来测定《左传》成书的年代,于此便没有选择昭公四年的“郑先卫亡”,而是根据陈氏代齐的预言推断《左传》成书的下限是田和为齐侯之前,即公元前386年,而上限则为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封侯之时的公元前403年,因为《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毕万之后必大”且被称之为“公侯之孙,必复其始”;于此,《左传》的成书年代应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②
在徐中舒、杨伯峻之后,这一种方法又被其他学者广泛使用、接受、确认,只是选择具体预言的范围又进一步得到改变、拓展、细化。与选择陈、魏两氏为侯的预言不同,赵光贤顺着徐中舒的思路,根据《左传》昭公四年所记蔡、曹、滕、郑灭国预言,特别是“郑先卫亡”的说法认定《左传》成书的上限是公元前375年,而文公六年所记的“秦之不复东征也”则指向《左传》成书的下限是公元前352年,因此赵光贤推定《左传》编定的年代当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52年。③与赵光贤推断年代时所根据的预言一样,赵伯雄却根据《左传》昭公四年“郑先卫亡”的验辞、文公六年“秦之不复东征”的不验之辞认为《左传》的成书时间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43年,④因为《史记·秦本纪》所记“天子致伯”才标志着“秦之不复东征”的不验,而此年正是公元前343年。与赵伯雄将《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所记卫国“卜日三百年”视为“不验的预言”不同,黄觉弘认为这一预言在卫嗣君时代得以应验,因为《史记·卫康叔世家》明确记载“嗣君五年,更贬号日君,独有濮阳”,而“更贬号日君”正意味着卫国灭亡,《战国策》记卫国事以卫嗣君结尾,也代表着时人对卫国灭亡于卫嗣君的认可。于此,黄觉弘根据“预言解证法”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限是卫嗣君五年,即公元前320年,而下限在魏襄王卒年的公元前296年,因为汲冢竹书《师春》卜筮事例引用了《左传》。⑤
显然,与其他论者相比,黄觉弘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限是根据预言的应验与否,而下限的时间是根据其他文本对《左传》的引用。他的这一做法已经表明,单纯使用“预言解证法”难以准确回应《左传》的成书时间。其实,在黄觉弘之前,王和已明确意识到由预言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局限性,他指出仅仅根据预言判断《左传》成书的年代,“其证据尚不够充分”,进而他主张结合《左传》取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笔记材料的“多寡”情况来判断成书时间,因为一旦国家灭亡或内部动乱、公室失权,原本属于秘藏的国家档案便会形成人尽可观的公开书籍,乃至“成为私人著述的材料”。①基于这一观察视角,王和认为《左传》中取诸史书的材料应该以郑、晋、魏三国为最多,这说明“郑先卫亡”的预言蕴含着《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即公元前375年;而“秦之不复东征”的不验预言,蕴含着《左传》成书的下限,周天子致胙于秦的时间是公元前360年,这一时间也与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论述的《左传》“岁星纪事”所实测的天象时间相应。因此,《左传》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60年之间。②在王和看来,尽管“不验的预言”可以用来判定《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却不能依据已验的预言来判定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因此他根据史料的多寡来验证“郑先卫亡”的可信性,并以此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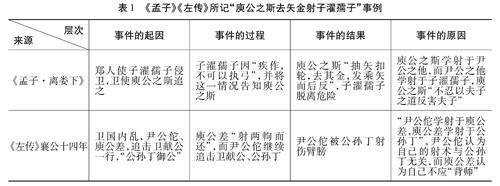
這一论证方式实际上仍然是“预言解证法”,只是通过《左传》史料的多寡情况来加固了相关预言的可靠性。其实,单单从史料的多寡来看,郑国的史料并不是最多,以黄觉弘的统计而言,晋、鲁、楚、郑、齐等5国的史料依次减少,③如果这一统计可信的话,楚国的史料显然多于郑国,而楚国灭亡又无疑在郑国之后,那么楚国史料如何传播至普通社会阶层则值得重新商榷。因此,以史料的多寡来增强预言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客观而言,既然《左传》所记预言的来源十分复杂,那么根据预言的验与不验来判定其成书时间,本身都是成问题的:既然《左传》所记预言的来源驳杂、作者不一、时代不一,那么无论是判断其成书时间的上限还是下限,都是不恰当的,其结论也是难以成立的。同时,每则预言往往只是针对个别事件进行言说,即使准确考察出与其相应的具体年份,那么也只是确定了这则预言形成或书写的年份,由此一则或两则预言的形成、书写年代进而扩展至《左传》全书的编纂年代还十分冒险。汲冢竹书《师春》卜筮纪事同于《左传》而又成为专书的现象说明,《左传》所记的卜筮或预言事例都可以单独书写、使用乃至播散、传承,即卜筮、预言事例具有单独流传的可行性和文本证据。
“预言解证法”的另一弊端是同一预言具有多种解释,进而便会形成不同的时间判断。这一现象在前述多位学者的推断中均有表现,如杨伯峻根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陈完“代陈有国”的预言.认为《左传》的编写者只是看到了“陈氏代齐之苗头”,而并没有看到真正代齐。④而赵伯雄根据此则预言认为其中已经蕴含着田氏代齐的事实,因此《左传》的成书应在此年之后。⑤同样,对于《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所言的“秦之不复东征”,陈茂同认为这不是预言,更算不上不验的预言,因为根据《史记·秦本纪》在秦穆公之后、秦孝公之前“秦屡出兵东征”,“不复东征”就是如同“叔向给子产书中的话与秦君子的评论同属因不满而发出的诅咒”。⑥而赵伯雄认为不能因为秦国与东邻作战就是“东征”,所谓“东征”应是指以争夺霸权为目的的大规模向东方用兵,因此“秦之不复东征”是一则不验的预言。⑦张固也却认为“君子感叹”的“秦之不复东征”是指秦穆公自己“没能继续东征,称霸中原”,这与君子日“秦穆之不为盟主”相通。⑧于此,“秦之不复东征”只是对秦穆公功业的评价,而不具有预言的意义。
与这两则预言的阐释近似,针对《左传》昭公四年的“郑先卫亡”,学界也有不同的解释,如徐中舒认为“郑先卫亡”是指“郑亡之后,不久卫也灭亡,先后不能相去过远”,⑨而赵伯雄认为此句意指《左传》作者已经看见郑国的灭亡,而没有看见卫国的灭亡,①并根据《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所记卫国“卜日三百年”,而卫国真正绝祀是在公元前241年,认定这是一则不验的预言,因此《左传》的成书应在僖公三十一年之后的300年至公元前329年之前,即“《左传》如作于前329年以后,作者是绝不会记下卫国将在帝丘延祀三百年这一不验的预言的”。②赵光贤、王和认为“郑先卫亡”的预言说明郑国已亡,而卫国未亡,但与“秦之不复东征”相比,卫国未亡的时间不能当做《左传》成书的下限。
与徐中舒、赵伯雄、赵光贤、王和的判断均不相同,黄觉弘认为《左传》的作者已看到了卫国的灭亡,所谓“卜日三百年”是指卫嗣君于公元前320年被贬为君,他的根据是《史记·卫康叔世家》“嗣君五年,更贬号日君,独有濮阳”,于此“郑先卫亡”之卫国的国运不但不是未验的预言,而且是已验的预言,因此卫国“卜日三百年”的时间也不能被视为《左传》成书时间的下限,而应该被视为成书的上限。显然,由于对预言本身的阐释不同,判断预言的性质、形成时间也多有差别。
如果考虑到这些卜筮预言进入《左传》的路途、时间等因素,那么必然涉及《左传》文本的组合、变动、系联乃至系年的过程,包括《左传》书写者的材料收集、筛选组合、编联排列等。而在这些过程中,书写者、编纂者本身对于卜筮或史事预言的主观认知、解读,无疑也是《左传》预言比较驳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左传》编者将“郑先卫亡”的预言,系于《左传》昭公四年郑国浑罕对子产的评价,而卫国“卜日三百年”系于《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两者系年的不同展示出言说重心的差异,系年的有别也昭示出两者具有不同的史料来源,于此两者也并不必然能够互动关联、前后相互照应以指向郑卫两国的存亡时间。退一步说,即使将两处的言说都视为应验或不验的“预言”,也仅能说明郑国浑罕的言辞形成于郑亡之后,而难以成为整部《左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同样,卫国都于帝丘三百年的卜辞,也仅代表著此则卜筮出现于公元前329年或公元前320年之前,却难以说明整部《左传》成书于这一时间点之前,更何况卫国灭亡的时间点本身就存在争议。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预言解证法”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是一种文本自证的方式,而文本自证则会忽略编纂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预言事例毕竟处于《左传》的文本书写之内,如果编纂者有意通过卜筮预言来掩饰、回护、遮盖所处的时间点,那么即使《左传》存在着被认定为未应验的预言,也并不能当作文本书写的下限。因此,结合“预言解证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左传》自载预言来判断成书时间的方式,是很值得反思的。
根据《左传》文本内证存在的自证局限性,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方式应该进一步审视和拓展,特别是结合当今所见大量出土文献的春秋史文本,《左传》在战国社会的史料来源、成书过程也得以观察得更为清晰、明确。
二、出土文献与儒家学者的德义追求
随着上博简、清华简、枣纸简以及慈利石板村“吴语”的发现、整理和公布,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春秋史文本应是那些呈“散编”形态的春秋史短章。目前所见,这些春秋史短章数量多样,内容丰富,书写风格活泼、灵动,书写文字尽管以楚文字为主,但书写内容并没有限制在楚国范围内,如上博简《姑成家父》《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景公瘧》《郑子家丧》甲乙等,清华简《子犯子余》《晋文公人于晋》《赵简子》《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产》《管仲》《子仪》以及枣纸简《齐桓公自莒返于齐》等,都涉及齐国、郑国、晋国的史事,这说明中原各国的史料早已传到了南方的楚国,以至楚国人将之转写成楚文字加以阅读、收藏、传承。如果以此再扩大视野,将多章连缀的春秋史文本也计算在内,那么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清华简《系年》、汲冢竹书《国语》以多章汇集的形态呈现,关注的史事更是涉及天下诸国,书写者没有明显的地域之别而以评判史事、明古今之变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