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曾经普遍实行的毕业留校制度,近年来逐渐被“非升即走”制度(up-or-out)——高校青年教师的“对赌协议”替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有近112所大学实行了以“非升即走”为核心的新型聘任制度。
非升即走,针对的是青年教师“讲师—副教授”阶段,采取预聘制,即达不到考核要求不再续聘。这个起源于美国高校的制度,初衷是让真正有学术潜力的研究者脱颖而出,通过授予终身教职给予高校教师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与生活保障,剔除想要混教职的人。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校将非升即走制度与青年教师的课题、基金申报数量、论文发表数量等单一标准紧密结合在一起,导致大多教师被规定的话题、领域和视角约束,甚至沦为发文机器,很难拥有足够的精力从事从自己的兴趣和问题意识出发的研究。
这种制度也导致青年教师不得不“重科研,轻教学”,很多学生也沦为给导师负责的课题打工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学术产出链条中最底层的一环。
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这一机制的问题,开始着手改变。比如,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退出了以论文影响因子为主指标的高校排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宣布将不采用“非升即走”等竞争性淘汰招录模式等。如果把这些学校的改革措施放在一条不同调整程度的光谱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将位列比较“激进”的一端,是个典型的案例。
2019年,赵鼎新担任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系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彼时他已66岁,是芝加哥大学讲习教授、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在他领导下的社会学系招募了大量“海归”学者,不少学者的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界并非主流;他鼓励学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但不以此为考核指标;在学生培养上对硕士生、博士生实施多导师制;在社会学研究方向上,他尝试建立一套不同的学术体系,为中国的社会学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并创建能与西方主流社科领域对话的社会学系。为此,他尝试自己筹集维持社会学系独立运转的资金。
2024年3月,围绕着浙大社会学系的改革风波,中国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本期杂志,赵鼎新与我们分享了他的改革原因、目的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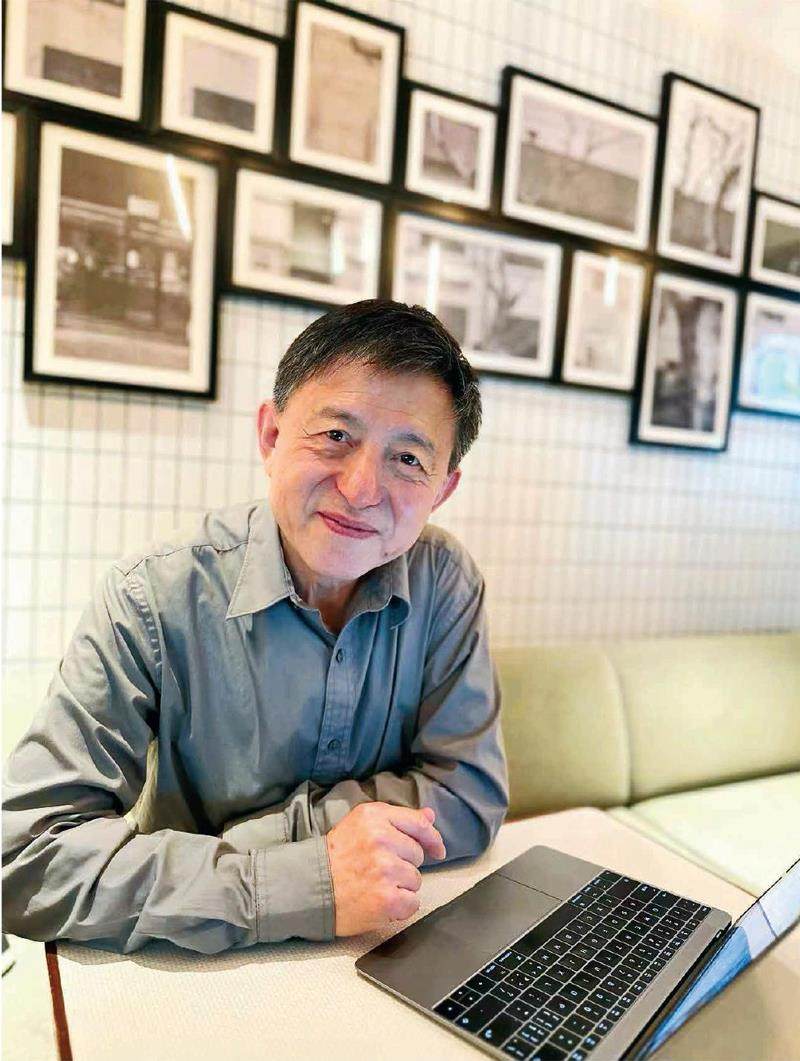
Yi YiMagazine
Zh 赵鼎新
Yi 当时国内的社会学人才培养、学术体系出了怎样的问题,让你想要去浙大改革呢?
Zh 中国留学生整体素质、英文越来越好,但你会发觉他们成为学者后在各方面跟不上西方优秀学者的水平,而且研究中国问题往往隔靴搔痒,总是没能抓住中国的一些核心问题。
我后来发现一个重大原因:西方的学术脉络,尤其像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发展到今天有其内在的逻辑,所对应的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焦虑,与中国的核心问题所在,以及中国学者的焦虑常有较大的距离。这就导致中国学者除非是天才,否则很难突破这一点,往往进入了他人的窠臼而不能自拔。而國内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写法上与国际社会学界有明显不同。
这就导致在海外训练得越好,回国后越难以适应。许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为了适应国内情况,几年下来,凡是转型成功的似乎在海外就白训练了,转型不成功的则活得非常不愉快。所以我就想创造一个能够训练一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老师,让他们能看透、突破西方学术的内在发展逻辑框架,同时又有能力把自己最好的研究通过西方最主流的大学出版社和期刊发布。
Yi 为什么会产生“白训练”的现象呢?是指他们受到了国内环境的影响吗?
Zh 1990年代中期后,国内社会科学学术环境变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量的教师要么转行经商,要么出国,要么忙着搞钱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大学环境由此变差,学者和学生也都越来越工具理性,而就在此时教育部开始发起核心期刊发稿量和排名评比,设立各种头衔、帽子,高度工具理性的学者则拼命抓头衔、抓文章。学术风气于是每况愈下。这样的环境对于在海外学成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难适应的。就目前来说,我认为最好的政策是教育部放手5年什么都不管,很多问题也许自然就能得到缓解,但问题在于教育部必须做事,不能“不作为”,所以很难论(它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