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新书《创新主义》由中信出版社在2024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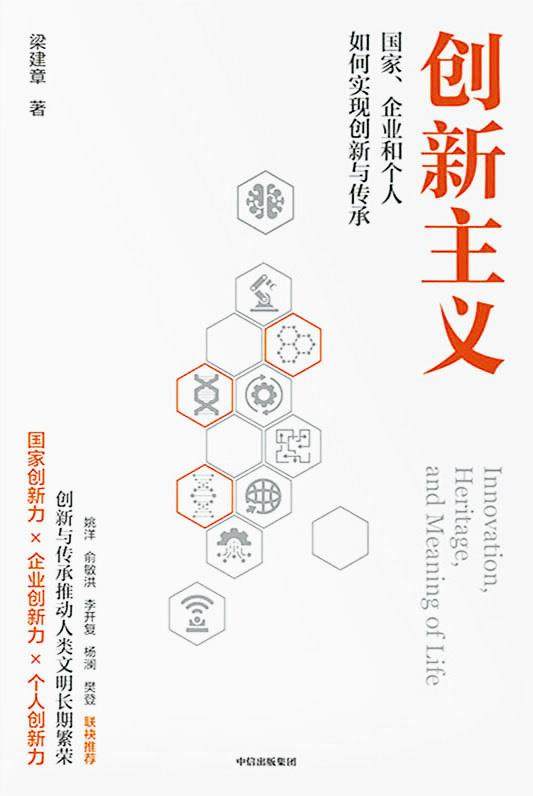
Yi YiMagazine
L 梁建章
01
Yi 你提出的“创新主义”强调生命和文明的传承,但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的现状是,年轻人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似乎更追求及时行乐而非长远的传承,更关注个体自由而非宏观层面的价值。你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现象?
L 是,我也注意到有很多人说相比当年的70后、80后,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奋斗精神,无论对工作、结婚还是生孩子都缺乏兴趣。这种“躺平”现象很像是1990年代日本年轻人中所谓“啃老一族”的困境。我在《人口战略》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总的来说,就是当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依靠努力工作逆袭前辈时,自然就会把兴趣放在娱乐等其他方面。当然,“躺平”还有多种原因,但是经济放缓和创新机会减少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认为在政策上社会资源需要向年轻人倾斜,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帮他们实现自己的创新追求。相比1980年代,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已经富裕了无数倍,我们可以用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来支持年轻人,让他们拥有更多的上升机会和发展空间,进而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少年强,则中国强,年轻人的困境同样是未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困境。另外,年轻人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躺平很快乐,但是不够高级,如果不生孩子、不努力工作,是可以让自己没有压力地生活下去,因为现在温饱不是问题。但这样一种人生,可能也是缺乏意义的。
02
Yi 这是否意味着个人主义与创新主义存在矛盾?如何理解代际利益的错配?
L 如果每个人从自己利益考虑,而非追求人类长期意义的话,生孩子也好,创新也好,个人的确辛苦。他只得到了利益的“小头”,而整个人类社会得到了利益的“大头”。比如在现代社会,由于有社会养老保障,人们可以不再依靠“养儿防老”,而且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生育孩子变成“损己利人”的事情。出于自身利益,是会少生,但每个人少生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付出严重的代价。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再比如新能源技术推广,它的受益者是年轻人和我们的后代,对年纪大的人来说,新能源推不推广,影响不会很大。以后海平面升个两三米对他们不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年轻人、下一代人会受影响。所以这其实是超越自我、超越当代人的一个价值取向。只有整个社会形成共识“环保是为了后代”并决定解决这个事情,才会有持续的投入。无论是鼓励生孩子,还是推广环保,都需要让我们的社会达成一种共识,也就是创新主义的共识。
03
Yi 創新主义强调人口和开放,而在如今强调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受追捧、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互相制衡仍然突出的背景下,创新主义是不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主义?它能否成为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共识?
L 从经济意义上,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创新已经成为核心活动。未来,大国的竞争是经济竞争,这与历史上的竞争完全不同。过去,竞争通常是一种零和游戏,国与国之间对领土和资源展开激烈的争夺,往往导致冲突和战争。今天,主要大国之间开展的是对创新和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已不再是零和竞争,因为创新不仅对创新者有利,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此外,人才的激烈竞争可以提高教育的投资回报,并促使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会造就更多的人才。但是,这依然是一个高赌注的游戏,毕竟世界上只存在为数不多的创新中心。当一个城市或者地区成为某一领域的创新中心时,就会比其他城市更具活力,也更加富裕。资源和土地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经济竞争体现为创新的竞争和对人才的争夺。不过《创新主义》这本书不是从经济层面,更多是从哲学层面强调,创新与传承是超越群体、超越国家的一种价值观念。我们今天能够思考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是我们祖先经过多少年不断的创新和传承,将人类的知识积累建设成了大厦,同时我们拥有了几十亿人,基因也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我们创新大厦的硬件,它也是经过许多年积累的几十亿人。我们需要把这样的火炬继续传递下去,实现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
04
Yi 如何理解人口和创新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人口的增长与创新活力的激发及经济的增长是完全对应的吗?
L 我提出的“人口创新力”模型概念,即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这和人脑神经网络的组织形式是很像的,神经网络由神经元的数量、神经元的强度和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强度构成,国家和企业也是如此,创新力取决于人的数量、人的能力和内外交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