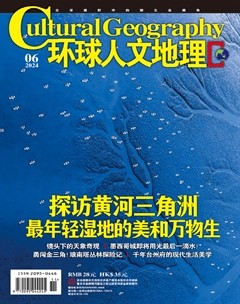能够把蛋炒饭叫做桂花饭的地方,想必生活里是有一种诗意侍候着,还透着能够对万事万物命名的自信。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把蛋炒饭叫做桂花饭了。想想也是,现在的人,凡事就讲直接,讲经济,讲成份。蛋炒饭三字既说了成分,又讲了制作过程,完全是一份简单明了的食物构成说明书。除了像我这样闲得无事的人,似乎已经没人在乎把蛋炒饭叫不叫做桂花饭了。
其实,桂花饭不仅仅是一种对待剩饭的态度,还是人类模仿自然的一种能力,更是把自己融入自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普遍反映在中国人对餐饮的做法,甚至命名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在农耕时期的文化遗产。我们越来越快地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过去的这种能力也正在减弱。
蛋炒饭有史可查,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上有关“卵熇”的记载。专家考证,卵熇是一种用黏米饭加鸡蛋制成的食品。熇字本义为炎势猛烈,这与蛋炒饭的做法倒是相符。又有说法,熇是用微火把汤汁煨干的一种烹饪方法,这似乎与蛋炒饭的炒不符了。专家们怎么讲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像我一样从农村考出来的学生,高考是件关乎命运的大事,自然会记得不少的细节。我参加高考的第一天早上,母亲给我做的就是桂花饭。记得米饭是头天晚上煮饭时特意多抓了一把米剩下的。那个时候,关于早饭的概念,在我们家里,日常是玉米面煮的拌面饭,大米煮的稀饭已是稀罕之物了,再朝大米稀饭往上,真不知道早饭该是什么做的,已经严重超出想象了。所以,高考时吃一碗桂花饭,已是全家人能够想象出的最好的早饭了。并且,能够保证一上午的考试不会因肚子饿而影响成绩。吃完一碗桂花饭,怕关键时候口渴,就用那碗,倒满满一碗的白开水喝下去。
1981年的高考,对一个农村户口的家庭而言,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眼睛高度近视的我,能不能跳出农门,会不会戴着厚厚的眼镜下地去干农活。桂花饭是用家里中等大小的碗盛的,冒了尖。吃完饭后的碗,一粒米都没剩,一丝蛋也没有,干净的碗里只有些零星的油珠,说是油珠,其实,已不能用珠来形容,只是挂在碗壁上的油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