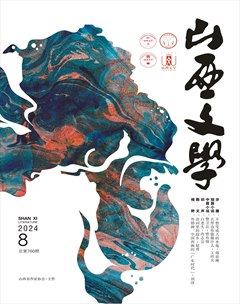起反
又写关于赵树理的文章,便翻阅新版《赵树理全集》(董大中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发现《“锻炼锻炼”》中有一个注释。当小腿疼在社员大会上交代问题时,她骂了杨小四一句。接下来,赵树理如此写道:“她一骂出来,没有等小四答话,群众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哗’的一下站起来:‘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骂人?’”注释加在“造反”处,云:“‘造反’,《火花》发表时作‘起反’。”(第2卷,第341页)
于是我给董大中先生写信,先交代这个注释,然后说:“其实我在看大众文艺版时也发现了这个注释,未查以前的版本是不是这样。现在想问您,这个注是您加的还是原来其他人加的?‘起反’是晋城那一带的方言,赵树理这么用是没问题的。改成‘造反’便于读者理解,但我觉得也让表达失去了一些味道。”董老师很快回复:“你说的《“锻炼锻炼”》那个注释,我不记得是怎么一回事。‘起反’是方言,我不知道,如果知道,会在注释中说是方言,现在这样注,给人原来排印错误的印象。”
在我的印象中,晋城话是不怎么说“造反”的,但“起反”却说得很普遍。查《现代汉语词典》,“起”作动词,有“发动、兴起”之意,如“起事”“起兵”。“起反”应该就是在这层意思上用起来的。
一个人气势汹汹过来吵架,晋城人会说:“干甚呢,你还想起反?”
小孩子调皮捣蛋,上房揭瓦,晋城人又会说:“小日母你还起了反了,我一脚踢死你!”
赵树理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使用“起反”的,他用得很地道。改成“造反”,意思大致不差,但比较硬,不如“起反”软和。词典中对“造反”的解释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动。”
同时,若把“造反有理”改成“起反有理”,感觉也不对。“造反”显得气宇轩昂,声势浩大,“起反”就弱了许多。
整工夫
赵树理在1955年发表《三里湾》之后,不久又写出一篇《〈三里湾〉写作前后》。此文首发于《文艺报》1955年第19号,自然也被收入好几个版本的《赵树理全集》中。《全集》中此文下面有一个注,注云:“1985年日本学者、和光大学教授釜屋修从《三里湾》日译者之一冈崎俊夫的家中找到了赵树理的一封信、一篇《代序的序》和本文的打印稿原件。从中可知,本文系应前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之约而写,为《三里湾》俄译本代序。赵树理在寄给冈崎俊夫此文打印稿原件时作了几处改动。本书据《三复集》,以寄给冈崎俊夫的打印稿作参校。”或许是因为“参校”之故,此文有十多处校对,但有个别校对弄错了,应该是编校者不懂晋城话所致。
例如,赵树理说:“过去在茶馆里说书的评书艺人是每说一段收一次费的;而听众又有些是有闲阶级(可以说是职业听众),每天可以误上整工夫来听书。”查始发刊物《文艺报》,赵树理这里说的就是“整工夫”,但《全集》中却改成了“整天工夫”,并作注道:“‘天’,打印稿缺。”(参见北岳文艺版《全集》第4卷,1990,第285页;大众文艺版《全集》第四卷,2006,第382页)。
这是一个明显的误校。
晋城话中是有“整工夫”之说的,例如,张三问李四:“有没有工夫跟我去锄会儿小苗?”李四说:“没有整工夫啊。”所谓“整工夫”,就是相对完整的时间。这个时间不固定,可以是一前晌或半后晌,也可以指两小时或仨钟头。
“误上整工夫”是一个很地道的搭配和表达,但改成“误上整天工夫”就不对了。而且,此句前面有“每天”,再来个“整天工夫”,逻辑和情理上似也不通。因为评书艺人说书,是不可能一说一整天的。
顺便指出,把此文中的“打擂”改成“打擂台”,感觉也不对。赵树理说:“例如有一本说秦琼打擂的评书,说秦琼一上了擂台就被早已要捉拿他的官府捉进狱里去,……”《全集》改成了“秦琼打擂台的评书”。省略“台”而单说“打擂”,在晋城话中是通的,普通话也这样说,何况说“秦琼打擂”,表达也更简洁。为什么以为这是赵树理漏了字,专门加一个“台”字呢?
赵树理被称作“当代语言艺术大师”的时间是1956年,其始作俑者是当年的“文艺总管”周扬同志。周扬把赵树理列于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之后,通称他们为“语言艺术大师”,自然有其特殊用意,但于赵树理而言,我觉得这个称号还是恰如其分的。对于“语言艺术大师”的文字,还是不要轻易改动为好。
得劲/不得劲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夕,赵树理写了篇《会师前后》,算是祝词,发表在当时试刊的《文艺报》上。他一下笔,就用上了晋城老土话:“会师之前,虽然大家都在艰苦作战,但正因为各有‘艰苦’,仗打得有点不得劲。”文章写到末尾,他又说:“要说我们过去的仗打得有点不得劲,那么会师之后,正是我们打‘得劲’仗的时候。”实际上,早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就用起了“不得勁”。其中老恒元对刘广聚说:“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点不得劲,想早点歇歇!”
这里的“得劲/不得劲”,原来我以为是晋城方言,但查《现代汉语词典》,它们都有解释。得劲有两个义项,一是称心合意,或顺手;二是舒服合适。不得劲解释有三:一、不顺手,使不上劲。例如:陈登科《活人塘》:“老百姓虽说摸不着底,可也看得出黄狗有点不得劲的地方。”二、不舒适。例如:茹志鹃《高高的白杨·妯娌》:“红英站着,正感到浑身不得劲。”三、不好意思。例如:老舍《四世同堂》:“看看那些出来进去的人,再看看自己鞋上的灰土,与身上的破大褂,他怪不得劲儿。”(例句来自“百度百科”。)
“不得劲”出现在这么多作家笔下,可见它并非晋城话所独有。
尽管把“得劲/不得劲”归入晋城话有些勉强,但我还是觉得只有用晋城话说出它们时,似乎才能把其中的舒坦或不舒服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就是在“得劲/不得劲”声音熏陶中长大成人的,似乎也很早就领略了这两个词的妙处。
比如大热的天,喝了一碗凉透了的绿豆汤,喝汤者一饮而尽后很可能会跟一句:“真得劲儿啊!”这种感叹,类似于现在的年轻人说“特别爽”。
小时候,我因常吃高粱面或玉米面圪条,常常烧心。一烧心就上头,一上头就圪脑疼,于是便跟老师请假,半后晌回家,不上学了。这时候奶奶就会问我:“又不得劲儿了?”
在晋城话中,无论是“得劲”还是“不得劲”,后面通常都是要加儿话音的。当然,十里不同俗,十里也不同音,我就听到过不加儿话音的说法。
回到赵树理,我总觉得他在作品中、在开会作报告的大小场合中不断用“得劲/不得劲”来描述人物或自己的心中感受时,其实已把它们普及开来了。例如,他在1960年8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上发言,题目是《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谈到最后,他说:“脑子里活材料积累得多了,写起来一联系就是一嘟噜,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点得劲之感。”
您瞧,又是“得劲”。这里的“得劲”应该是下笔左右逢源,如山涧泉水,咕嘟咕嘟往外冒。
孙谦说:“赵树理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赵树理当时确实没用所谓的“方言写作”,但偶尔也能捎带出一点晋城话。不熟悉山西方言晋城话的外地读者,自然也能明白其含义,但要读出其中妙处,读得“得劲”,恐怕还是上党革命老区一带的读者最有感觉,也最能心领神会。
不歪
拙文《不成样子的缅怀——“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推送后记》中有句“写得不歪”,引起了一些恐慌。
最初我在“征求意见稿”中夸一位远房师妹,说读过她的文章之后,觉得写得不歪。意见征求过去,她疑心生暗鬼,问:“不歪”是啥意思?是说我写得“尚可”?或者是写得太“正统”?
我大笑,于是给她解释一番。
但征求完意见后,我把夸她敲打她的话都删了,只保留了写方锡球教授那处。
我说:“当我读到结尾句‘我忧郁地低下头,再抬头,就看到站在一旁的程正民老师泪眼矇眬’时,就觉得笔法果然老到,桐城派韵味呼啸而出。但我有必要夸他吗?于是我惜墨如金,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写得不歪!’”
这个“不歪”,很可能也让我们的老方同志比较晕菜,估计他心里嘀咕:这究竟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是夸,但这是我们老家一带的夸法。
在我的印象中,晋城人是不大习惯说“很好”之类的“普通”话的,他们夸人夸物夸事,往往喜欢“不歪”。
某人家境殷实,贫下中农会说:“人家那小日子过得不歪。”一脸的羡慕嫉妒恨。“日子”在晋城话中完全是另一种读音,我无法描述。
大姑娘眉清目秀,葱俊挺拔,媒婆便有了说道的理由:“人家可是长得不歪呀,你还挑甚呢?”
农村唱大戏,有人遇到鬼打墙,走了一黑来,第二天他问:“唱得怎么样?”“不歪。李玉和宽音大嗓门,唱得真不歪!”
在“不歪”前加上一个“真”,便可强化语气,增加分量。老式晋城话中没有“很不歪”这种说法。用“很”修饰“不歪”,别扭。当然,更不可能用北京人喜欢说的“特”或“倍儿”了。“超”是新新人类用语。
语气更强烈时,就成了“真真不歪”。为了验证记忆,我上网搜索,马上就弹出一个晋城媒体做的报道,题目是:《晋城人这个元宵节“闹”得真真不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