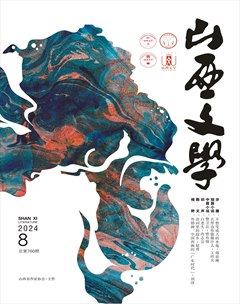槲寄生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周教授、马教授在临江市火绒沟村三社东南山坡上,见到一棵三四米高的山荆子树上,长着两簇槲寄生,一簇结的是红色果实,另一簇结的是黄色果实。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和马教授去红土崖镇至六道江镇那段山岭考察。站在山顶俯瞰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在最急的大拐弯处路旁有棵大青杨,树冠上密密麻麻地长着二十几个颜色较深鸟巢一样的球状物。我俩来到大树近前,发现那些“鸟巢”都是槲寄生。茎叶黄绿色,皮革一样的叶子泛着亮光,在茎枝分枝处结有晶莹剔透的橘红色浆果。细看槲寄生的果实呈圆球形,直径六到八毫米。
九月的槲寄生浆果已成熟,因为有很多树叶遮挡,很难看见它的影子。等树叶落尽了,槲寄生的果实在蓝天衬托下特别扎眼,吸引鸟儿飞来啄食,灰椋鸟、太平鸟、小太平鸟、棕头鸦雀等,都特爱吃它的果实。槲寄生的果肉很黏嘴,鸟儿吃完之后找块树皮,将小嘴不停地蹭来蹭去,就会把槲寄生果肉里的种子蹭到树皮裂缝中。也有的种子是鸟儿吃完槲寄生果实排泄到树皮上的。种子慢慢地萌发,从树皮裂缝向里生出寄生根,从树木的木质部中获取营养。种子一般要孕育三到五年,在漫长的等待中积蓄着某种力量,一旦种子感觉时机成熟了才开始萌发。
槲寄生是半寄生植物,它生命的养分,一方面仰仗寄主体内的寄生根,另一方面来自四季常绿的绿枝叶,能与太阳对话,进行光合作用。
槲寄生、大树、鸟儿在它们搭建的生态链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在大自然中不停演绎着,宛如一幕幕唯美动人的童话故事。
白山市周日的大集总有人卖槲寄生。我每次赶大集,见到那个卖槲寄生的摊位都要停下来,不买也要蹲下欣赏一番,闻闻那些汲取山林精华的一簇簇枝叶散发出的清爽气息。在冬天里,每次欣赏这种四季常青的植物,总有种神秘又亲切的感觉。毕竟这种在我的家乡辽宁新宾被称为冬青的植物,自己小时候也采过它,一点儿也不陌生。想来山里长大的孩子,与许多植物都有独特的交情。
软枣猕猴桃
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子、圆枣子。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临江溪谷的一个山坡上,我用树棍钩下来几颗圆枣子,已熟透发软,只是未经霜冻,果皮依然是绿色。我想分给周教授几颗,他专注于拍摄,我全吃了,香甜无比。我端详那棵软枣猕猴桃的枝叶,宛如由绿叶与金黄叶子编织成的挂毯,天然靓丽。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我与几位诗友去临江岭上枫林,在树林与山顶草甸交界地带,我们找到一棵软枣猕猴桃,树叶落光,地面落叶中捡到几颗圆枣子,经霜打已变黄褐色,稍显皱巴了,不过吃起来特甜。我们使劲晃了晃树藤,又落下了一二十颗。回来后,我特意写诗记之:“都说岭上好,偶与友朋邀。牛阵盘山下,鹅群展翅摇。晃藤拾软枣,拨叶找核桃。晒尽烦心雨,暖阳把手招。”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诗友杨殿军带我们到市区北郊的青山湖,在湖西岸的落叶松林里,找到了他早先发现的那棵软枣藤,攀爬在一棵高大的落叶松上,能看见上面结了不少圆枣子。软枣猕猴桃仿若有意让自己的果实越来越往高处长,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基因里好似都有一句代码:“要让人类够不着。”可这次也没能难住我们,五十多岁的杨殿军自告奋勇,很敏捷地爬上树,大家惊叹不已。他在树上轻勾慢打,落下了不少圆枣子。我和其他几位同伴在树下捡,蔫巴成黄褐色,样子难看但甜软。看来圆枣子不怕冻,经过霜冻才能更甜,有如我们过的生活一样,经历得越多,品起来越有滋味。
二〇二〇年九月的一个周末,我又来山货庄周边的集市转。见到几个摊位都在卖圆枣子,其中有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身材如男人一样魁梧,穿一身绿色旧军服,脚蹬一双靴子,身旁放着一个编织袋做的背筐。她坐在马路牙子上,面前平铺的编织袋上放着刚采来的一堆圆枣子,其中有些是连着藤枝一起砍下来的,还没来得及细摘。她和旁边的熟人边卖货边闲聊:“为了这点破玩意儿,差点要了我的命。”
听了她这句话,我这才注意到她眼眉上方前额中间横着有一道很长的血凛子,一定是采圓枣子过程中,不小心从树上出溜下来时划伤的。就冲她的这道新伤,我就买她的了。称了二斤,拿回家放塑料袋里边捂边吃。
味觉记忆神奇而美好,每个味蕾被圆枣子滋润过的山里孩子,都会对它有种独特的依恋。
小时候,秋天随大人上山,见到圆枣子必采。如果它还是硬的没熟,没法吃,就采回来放在小缸里捂,有时铺些黄花蒿,用它来催熟。捂一两天,圆枣子恍如经受了一段酷刑,终于开始服输告软,这时就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