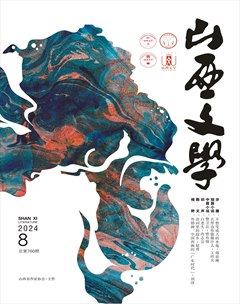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广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的对外贸易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西方世界为了打通中国的经商之路,在广州相继建立“商馆”,广州出现了带有西洋风格的绘画热潮,并且具有贸易品性质,人们将其称为“外销画”。它的兴起,除了显而易见的商贸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人对清朝中国的认知密切相关。伴随中西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中的美术作品,随着洋商船只远销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隨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商人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力量,大量迎合西方游客喜好的绘画在广州应运而生,构成了中国油画的“广东时代”。
一
自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以来,欧洲人加快了对整个世界探索的步伐。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关于古老东方帝国的奇妙想象,伴随着欧洲传教士的宣传被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西方人的脑海中,一定要塑造出一个虚化而完整的中国影像。正如英国学者赫德逊(W·H·Hudson)所说:
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幻想的中国,一个完全属于臆造的出产丝、瓷和漆器的仙境,既精致又虚无缥缈,赋予中国艺术的主题以一个新的幻想价值。(《欧洲与中国》[英]赫德逊著,王遵衷译,中华书局1994年9月出版,第250页)
这个“虚幻而完整”的影像终于在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各种精致美妙的工艺品中变得越来越真实。早期由传教士传递的新世界各种信息的使命,此时更多地由商人、旅行家和冒险家勇敢地承担起来。所以,欧洲人搜集中国的图画,不仅仅是为了旅行纪念,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对古老华夏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对来自欧洲的建筑学家、地理学家、动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商人来说,带回去的信息将更加完善了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当然也包括古老的中国。
乾隆22年(1757年),大清政府下令关闭除广州之外所有的通商口岸。于是,广州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就使广州的对外贸易进入一个繁荣的时代。西方世界为了打开通向中国的经商大门,先后在广州建立“商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于是,“外销画”在商业繁荣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成为专门销售给外国游客或商人的商品,而且迅速成为抢手的热门货。“外销画”内容丰富,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以展示当地的手工业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为主。尤其是对外国游客了解中国的传统生活和工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8、19世纪的广州,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唯一的窗口。广州口岸的市井风情,给那些前来羊城的外国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19世纪初的一位美国人曾经记述了他在广州居住时,在夷馆广场看到的社会众生相,包括卖咸橄榄、卖花生、卖糕点、卖茶水以及卖其他吃喝的小商小贩。瞬间转眼再看,还有卖滑稽曲本、变戏法,以及鞋匠、裁缝、翻修油纸伞、编制细藤条等各种各样的商贩。这位美国人在珠江航行的船艇里又看到另一类生意人——工匠、鞋匠、木匠、卖故衣、卖食品、卖饰物的人,还有算命先生、应急郎中、剃头匠、爆玉米花和专门给人洗头者。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这些生意的叫卖声,连同这些贩夫走卒,形成了一幅幅独特的市井风情画。1858年4月17日出版的英国《时代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拥挤的广州街道》,文章详细记述了广州街道拥挤的情景:
我们走进一个类似市场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令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很小的鱼市……我的向导不让我驻足,甚至可以说,他硬推着我往前走,一直走到浆栏路(Physi Srteet)。当我走进这个深渊时,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生出那种淹人欲死的感觉,头脑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夹在两排房屋间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被推着往前走。我毫无知觉,什么也看不见,完全被人山人海的人流所淹没;剃掉一半的头发、长长的辫子、长短不一的罩袍、黄色的脸、正在给自己扇扇子的人。我像只僵尸一样随人流蹒跚而走,或像一根树干一样随波逐流!……在这群人流中,我们未见到一个妇女、一个小孩、一辆四轮马车、一辆货车、一匹马、一只狗或者一只猫。我们见到的只是男人——到处都是男人;穿丝质长袍的男人、戴尖帽的男人、正在给自己扇扇子的男人、搬运货物或抬轿子的男人。(《18—19世纪羊城风物》,广州市文化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第34页)
这些社会众生相,构成了当年广州“外销画”创作的主题。而市井风情却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正如一首打油诗所写:“出门见摆满街头,有人叫卖四巷走。求神拜佛与占卦,五花八门无不有。”从历史的意义上说,美术作品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再现,也是历史的证据。从“外销画”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中,我们感受到艺术见证历史的真实性。在那些“外销画”中,我们仿佛听到当年广州街头喧闹的叫卖声,仿佛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体现出广州口岸独特的风情与习俗。
众所周知,历史是瞬息万变的,成就一段历史,不单单只是社会背景,还有当时一些艺术作品所反应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在西方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与东方不同的遗迹。那么,这些遗迹又怎么能代表西方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呢?也许,我们可以从那些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找到答案。甚至会在作品中寻找到历史的证据——从美术作品的细节中判断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未被发现的方方面面。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在广州口岸出现的“外销画”,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因为它们具有贸易品的性质,所以被称为“外销画”,还有的将其称为“贸易画”。这些作品基本出自中国画家之手,其中有油画、玻璃画、水彩画、水粉画等,随着外洋商船销往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商品。而“外销画”的兴起,除了商业目的之外,在当时也是欧洲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有些作品展示了广州的地方工艺,有些则表现了广州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产品。如今,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老广州的市井风情早已消失。但是,当年的那些作品,仿佛又将我们带回那个遥远的时代。
“外销画”西方化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中国的供画商与西方的商人都认识到,某些题材在西方客户那里会更受欢迎。事实上,“外销画”远比“外销瓷”的发展缓慢许多,作为商品远不如“外销瓷”销售的范围宽广——中国制造的顶级瓷器很快受到西方商人的认可。当中国的瓷器运到欧洲之后,受到西方人的高度赞美,洋人对中国瓷器爱不释手,赞不绝口,甚至直呼“china porcelain”。由于中国瓷器制造者的技术娴熟,所以出口瓷器的市场从16世纪开始,始终处在一种供不应求的繁荣状态。而中国的绘画在欧洲市场的接受程度却远不如瓷器那么乐观。17世纪90年代,当时的外交使节曾做出精彩的分析:
除了那些雪亮的一船船一柜柜的瓷器之外,中国人同样还会用画装饰他们的居所;他们并不擅长这门艺术,因为他们不钻研透视,尽管他们很努力地绘画;他们感到乐在其中;而且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画家……他们到处悬挂古人的画作,还有一些地图和一些白色缎子上的绘画,他们在这些缎子上画花草、禽鸟、大山和宫殿;其中有的画面上以大字题写一些有关美德的句子。 (《文明的维度》,吕澎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第132页)
尽管那些来到广州的欧洲游客无法欣赏中国绘画的技法,但还是有个别人能够感觉到,自然历史题材的中国绘画符合自己的审美。尽管他们为中国画家在绘画上缺少阴阳或透视而感到不足,但他们在中国画家的一些花鸟鱼虫作品的着色上发现,中国人在绘制上带有一定的准确性,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视觉效果是欧洲人所不及——甚至他们在描绘一条鱼时,会耐心地数清楚鱼身上到底有多少片鳞,并且在画面上准确无误地描绘出来。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对西方人来说,从遥远的中国带回去一套由中国人绘制的图画,除了具有纪念意义之外,还能更为真实地展现出这个东方古国的风貌。由于外国画家不通中文,他们笔下的中国就会带来很多的错误,而且大部分到中国的西方游客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无法深入了解中国人不同层面的生活。因此,委托当地人绘制具有知识性的绘画作品,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欧洲游客来说,中国人笔下的广州图像是最真实和最准确的资料,通过图像传达的中国信息逐渐从西洋画家的手中转到“外销画”的画家手中,由此构成中国早期“外销画”的知识性内容。
相关史料记载,18世纪的欧洲市场,曾兴起过一场“中国热”,中国的工艺品——漆器、瓷器等成为非常热门的外销产品,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而这些产品主要集中在广州口岸,随着来华外国游客数量的增多,自然形成了贸易绘画的需求,台湾学者傅乐治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记述道:
在靠岸停泊期间,他们将大批丝绸、茶及瓷器装载到船上,同时水手们也必定去寻找、换取或购买礼品,以便带回去送给家人或亲戚。他们购买的物品中,有一项便是绘画,其中又以壮丽的风景画或是人物画像,最受欢迎。主要是这些画的题材,都是中国山川风物,却具有西洋绘画风格,但都是由中国艺术家们手绘而成的。这些画的购买者多为西洋人,所以我们称这些画为“贸易画”。(《中国的贸易画》,《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第11期)
当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时,随之出现了一批绘制西洋画的中国画家,他们专门描绘中国社会的风物和广东沿海的风土人情,绘制大批油画、水彩、水粉和玻璃画。让那些前来广州的外国游客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东方古国的万种风情。洋人对这些手绘的贸易品爱不释手,加上价格便宜,于是争先恐后购买,慢慢地成为诸多商品中的抢手货。然后经外国的商船运往欧洲。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外销画”在广州沿海展现了极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外国人到此地所必须光顾的地方。到18世纪末时,广州珠江北岸专门经销中西贸易的“十三行”地区,已经形成绘制“外销画”的中心,而专门经营“外销画”的店铺也逐渐增多,19世纪初时,珠江北岸一带已经有经营“外销画”的店铺30余家。这样的规模无疑成为继清朝宫廷之后西画东渐的又一聚集地,也在日益繁荣的贸易中形成了中国早期油画的“广东时代”。
18、19世纪的广东“外销画”,迫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广州口岸的历史,它不断地提醒我们要理解口岸文化的基本形态,就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口岸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却共同参与了世界性的发展进程。尽管历史文献对广州出现的“外销画”还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那些精美的作品去感受一个时代的经济与文化,以及它开放而多元的文化生态,甚至从中了解当年广州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种种方式。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外销画”的形成、发展与壮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它是由贸易塑造的,而且每个不同的时期,都有其历史和艺术的特点。
二
刘海粟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近代美术史家把我的同时代人尊称之为先驱,我附在骥尾,惶悚不安,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大一些,中国油画史还可以提前半个世纪,真正的先驱,应当是被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埋葬了的无名大家,蓝阁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想法,希望能被美术史家所证实”。“中国油画史还可以提前半个世纪。”事实上,刘海粟的判断早就得到证实。正是伴随广州贸易而出现的“外销画”,使中国油画在沿海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外销画”,是1949年之后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开始使用的一个词汇。从18世紀末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生活在广州的中国画家也知道他们绘制的作品卖给了洋人,但是在当时,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还没有将这些作品划分为“外销”或“内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