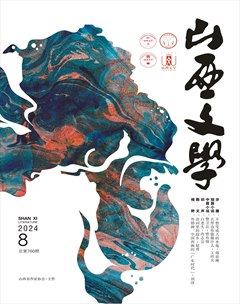《五月》之风
从事文学编辑、批评写作数十年,在文坛上社交也广,识人颇多,交友不少。有的人曾经过从甚密、朝夕相处,但后来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了;有的人只是偶尔相识或几面之缘,却心灵相通,成为师生、朋友、知音,让人没齿难忘,终生感念。我与田中禾先生就属于后一种情形。
上世纪80到90年代,田先生是《山西文学》的忠实作者,与刊物保持了十几年的“交往期”。我是刊物的一名编辑,与他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又有数天的接触、交往。就在这书来信往、短暂交集中,我们由文学关系,升级为师生加朋友的关系。我在阅读他的作品、信笺乃至思想、人格中,感受到了他的纯正、温厚、超拔的精神品格,就像一脉清流,从中原流到三晋,流到我的心里。
回顾1985年,那真是一个《山西文学》的“田中禾年”。而他是河南作家,并非山西作家。我1982年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忻州地区文联,在一份名叫《春潮》杂志(《五台山》前身)做编辑。我和同代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发展,但到1985年,新时期文学已在悄然分化、变迁。田先生的短篇小说《五月》发表于《山西文学》五月号。“五月”对“五期”,无缝连接。主编周宗奇特为小说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编稿手记”,曰:“读着《五月》,一股纯真之气扑面而来。最可贵的就是作者完全从自己所观察到、所理解到、所熟悉了的生活出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当今农民的多层次、多色调的生活图画…… 正是通过这些充满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的活生生的图画,使人们在一种美的享受之中,清醒地认识了当今的农村现实。”这段编者的话有几个要点:一是认为小说所展现的世界是作家主体所感受、所创造的;二是这幅乡村图画是多层次、多色调的;三是小說具有纯真之气、诗意之美。细细品味,可谓“一语中的”。
19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刊物发行量巨大。《五月》像温煦的夏风,在山西文坛、三晋土地上涌动,乃至“刮”向全国。《小说选刊》 第7期转载,《新华文摘》第9期转载。《山西文学》第8期发表雷达的《〈五月〉的感想》,《红旗》第15期刊登张石山的《成熟在丰收时节——读田中禾的〈五月〉》。我所在的忻州地区,文联内外的作家、文学青年都在传阅、谈论《五月》,省作协的作家、编辑到各地市下乡,所谈所议也是田中禾和他的《五月》。此时的田中禾先生已从社会底层挣脱出来,进入河南唐河县文化馆工作,已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诗歌之类,再度复出文坛,但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一位外省作家在《山西文学》发表作品,受到如此“厚待”,似乎还从未有过。再说《山西文学》自有其传统,譬如乡村题材、地域特色、跟踪现实等等,亦有众所公认的建树。《五月》所以受到编辑、读者的“追捧”,一定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此时我已投身文学批评写作,细读了《五月》,深感这是一篇非同一般、内涵特别的小说。小说以农村改革开放为背景,描述大学毕业留在外省教书的香雨,农忙五月回到故乡参与家里的割麦、打场、卖粮等一连串劳动。但作家并没有直白地歌颂农村的新政策、新气象,而是提出了农村、农民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突破了主流小说的思维模式。小说写了父亲、母亲、奶奶、改娃、大狗、小伍等不同代际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归来的城市人香雨的形象,但作家却扬弃了现实主义那种个性化、典型化的方法和手法,突出了人物身上混沌的人性特征——即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胶着与矛盾,使人物显得格外自然、逼真、丰富。艺术形式上则运用细腻、真实、从容的写实主义方法,并赋予自然、人物一种诗情和画意,努力呈现出一种生活自身的原汁原味、固有样态。它是现实主义的,但又突破了现实主义,它是浪漫主义的,而又把它深蕴其中,它甚至有着现代主义的某种内核与色彩。当然作家还处在探索时期,作品还显得有些粗疏、生涩。这样的小说,与山西当时的乡村小说是息息相通的,但又超越了山西的某些作品,因此受到了思想开放的《山西文学》主编和编辑的“青睐”。若干年后,青年学人吕东亮指出:“ 《五月》鲜为人知地启示了三年之后‘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虽然《五月》没有被归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而落于文学史著述中天然安放的境地。”(吕东亮: 《“新写实小说”的先声——重读田中禾短篇小说〈五月〉》,《莽原》2022年第6期)其实,当时就有论者把田中禾归为新写实小说作家,但对《五月》并未作出精准的阐释。田中禾小说的复杂性,新写实理论也是难以涵盖的。
紧接着到1986年,《山西文学》第10期推出了田中禾的中篇小说《秋天》,同样是头条,另一位主编李国涛也加了“编稿手记”,他用鲁迅式的“哲思”语言概括了作品的故事情节,指出了其中“不够浑然”“有点生硬”的地方,然后说:“ 《五月》之后,田中禾毕竟不负众望,再一次为《山西文学》的读者们拿出自己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在努力而可贵地突破着自己。”这部小说以年轻考古者在河南盆地发掘汉墓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农家三代五口人在农村变革中的不同人生状态与命运遭遇,小说同样使用了新写实方法与手法,斑驳陆离,发人深思。这一时期,《山西文学》还发表了两篇评论,一是孙荪等的《〈五月〉漫话》,二是郑波光的《从“五月”到“秋天”》,在研究田中禾小说上有所深化。
田中禾是从《山西文学》脱颖而出的,这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并没有慢待他的故乡的刊物,如《莽原》《奔流》等。也没有忘记向全国文学刊物“冲刺”,如《上海文学》《人民文学》 等,并屡屡在这些刊物的评奖中获奖。
1988年4月,姗姗来迟的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田中禾的《五月》以19篇中的首篇位置获奖。从1978年到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过八届,《山西文学》以及前身《汾水》,获过三次奖,分别是成一的《顶凌下种》、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和田中禾的《五月》,田中禾是唯一的外省作家获奖,且独占鳌头。这让山西文学界喜出望外、颇受鼓舞。山西文学界与河南文学界都进行了祝贺、宣传!1989年,作为全国短篇小说评奖评委的宋遂良,发表文章称:“我虽然对去年的全国小说评奖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对于评委们一致将田中禾的《五月》列在获奖短篇的榜首,还是感到由衷的欣悦和钦佩的。”(宋遂良:《沉沦·困惑·悲愤——评田中禾近作三篇》,《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
从1985年始,我就喜欢上了田中禾先生的小说、散文,只要在报刊上看到,就会悉心阅读,收藏起来。我从一些有关文章、资料中得知:他19岁上高中时就出版了诗集;青年时从兰州大学中文系退学,落户城郊农村,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自修功课和坚持写作;流落底层后,创作一度中断,直到新时期之后才重新执笔,“一鸣惊人”……这些传说故事给田中禾先生增添了传奇、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