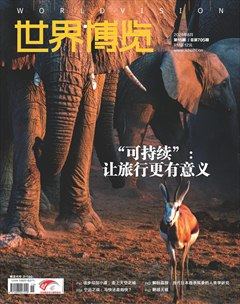初遇兴城,在2000年左右,漫漶的灰色似乎是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四座幸存的古城池之一,此地建起颇为时髦的仿古一条街。灰蒙蒙的细雨里,青砖地面上,红漆与灰顶构成主色调,外围土黄色城墙上瘢痕累累,颇为惹眼,但角落里横七竖八的自行车与半空中纵横交错的电线杆,不免些许出戏。几年之前故地重游,古城修葺一新,“袁”字令旗在城头飘扬,一排“锈迹斑斑”的红夷大炮瞄准城外天空,可惜它们来自河北曲阳的仿古作坊,明朝天启皇帝敕封的“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不知湮没何处。这位大将军,既不是袁崇焕,也不是某个辽东名将,而是一门在宁远之战里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夷大炮。
宁远之战
明天启六年(1626),平静四年之久的辽东喧嚣起来。隆冬正月,天寒地冻之时,努尔哈赤大军压境。总揽东北防务的辽东经略高第下令驻守锦州、大凌河一线的明军疾速撤回山海关,打算据险迎敌。官小位卑的袁崇焕却决意抗命,誓言与关外的宁远城共存亡。这座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一度毁于地震,后在袁崇焕主持之下重新翻修,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堪称山海关最为坚固的桥头堡。这位熟读兵书的将军深知,失去宁远,山海关就会沦为一座孤城,失败只在旦夕之间。袁崇焕从兵书上学到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他亲自杀牛宰马,以佩刀割肉,分给守城将士,又刺破手臂写下血书,对众人下拜道:“苟能同心死守,吾为牛羊以报!”
哀兵必胜,但仅凭士气并不足以御敌,袁崇焕早已料定,守城胜负的关键是架设在城外演武场的十一门红夷大炮。大炮身世,说来曲折。明末闽粤动荡不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轮番逡巡海上,对沿海港口虎视眈眈。在与这些红夷屡次交手之中,明朝官员切身感受到火炮之利,故而偷学其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萨尔浒一战已经证明,笨重缓慢的火器,根本不是八旗迅捷铁骑的对手。有此教训,徐光启、袁崇焕都信奉以大炮守城的改良战法: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有部将提议用锻铁封住城外火炮的火门,以免便宜了敌人,但袁崇焕力排众议,率领军民将红夷大炮挪至城墙四角,建筑炮台,专待来犯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