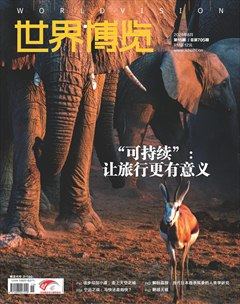陶渊明毕生都在追寻,有人说,这追寻就是“隐居”。毕竟,千百年来,陶渊明在中国文人心中,早已与“隐士”二字紧密相连。然,古往今来,“归隐”也多有引人争议的地方。“终南捷径”说的就是以隐居来博取关注、功名的“投机”路径。
于此,陶渊明可能不太一样。苏轼这样评价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故而苏轼又赞叹:“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是的,陶渊明是真诚的,不止于对他人,更可贵的,是对自己——他毕生都在真诚地探索自己,亦在“归隐”中追寻着内心真正的喜乐。
真诚的探索
对自己真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易。首要的问题是:你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人吗?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会以怎样的方式过这一生呢?
我们“见”过太多“与自己撕扯”的人。蘇轼也有“撕扯”的时候。贬谪生涯的同一时期、同一地点,他有白天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也有夜晚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慨叹“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当然,陶渊明也有矛盾之时。在他的诗作中,“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是对自己的年少时的认知——健壮且性情刚烈,可持剑只身去远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是对自己当年那番理想与壮志的悲忆——时光把人抛,毫不留情,奈何时代如斯,现实如斯。只是,他的文字中,没有“仰天大笑”的情绪跌宕,亦没有“长恨此身”的怨愤难耐,更多的,是一份理性与哲思。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东晋偏安东南一隅,内斗不断,战乱频仍,后又开启了改朝换代——宋、齐、梁、陈的乱世之旅。陶渊明便生活在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
在这样的时代里,青年陶渊明也曾相继出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官职,中间夹杂着“官场失望、回归田园、再展抱负”往复循环的内心曲折。他在几轮“出仕”与“归隐”中探寻自我,直至最后一次出仕,即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真正认清自己,挂印归田,正式开始归隐生活。《归园田居》组诗即作于他正式回归田园后不久。而陶渊明到底认清了自己什么,从《归园田居·其一》中我们可窥见大致答案。
一是认清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从少小时起就没有从俗的气质,天性就是热爱自然的。之前是误入了仕途的罗网中,转眼间就过了几十年。然就像笼中鸟依然留恋着过往的山林、池中鱼总是思念着从前的深渊,“我”的内心其实一直都是想去过田园生活。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铺陈的曲折,更没有对自己另类的标榜,读来只有认知自我的冷静与客观。
二是认清自己到底喜爱什么。田园生活多么美好啊:“我”有十余亩地,还有八九间茅草屋,屋后是榆树柳树的树荫,院前是满树的桃花与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