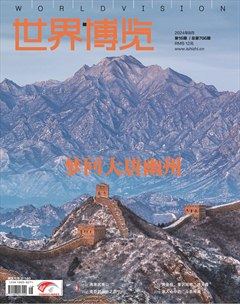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稀少。1981年,考古工作者对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边存在已久的一座墓葬进行抢救性挖掘,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唐代大墓。可惜的是,被破坏得几乎是一座空墓了。仅有的出土文物中最吸引人的是鎏金铜坐龙,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则是一批残破的汉白玉谥册,玉册上面出现“帝朝义”的字样,证明这是史朝义给父亲,曾经的范阳节度使史思明营建的陵墓。
史思明墓是北京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唐墓。不过,史思明的“帝位”不为后世所承认,且墓葬损毁严重,人们更愿意将“最高等级的唐墓”这顶桂冠置于刘济墓的头上。


晚唐幽州节度使刘济(757—810)墓出土了许多玻璃器,通过现代科技的成分检测,其中两件钠钙玻璃珠的化学成分显示其来自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这再次证明大唐幽州城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节点。刘济墓的一大亮点是壁画,画面上的芭蕉、仕女、黑马、宴饮、游乐……向后人勾勒出唐代贵族的生活场景。墓中的墓志、文物、壁画和中原唐墓没有重大区别,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示唐代的幽州城,在地域特色和王朝共性之间找到了一条新路,政治、经济、文化实力都有长足的进展。在这些文物的背后,是一个蒸蒸日上、突飞猛进的大唐幽州。
当大唐王朝攀登盛世之时,幽州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不仅因为大一统为经济繁荣降临北疆奠定了大的环境基础,更因为大唐融合宇内、跨越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胸襟与胆魄,完美地契合了幽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幽州城还将这种优势发扬光大。唐王朝的眼界与脚步,在东北方向以幽州城为据点,又跨越了幽州城,冲向更广阔的舞台。
幽州城的崛起
幽燕大地是东北、塞外、华北、渤海和山西五大区域交通的汇聚点——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再次增强了幽州的优势。作为农耕文明的最北缘和经营东北的据点、游牧文明的最南缘和进军中原的前哨,两种文明在燕山南北碰撞交融,共同塑造了幽州城。
幽州的区位优势,在中原王朝看来首先体现在军事价值上:“中国得之,足以蔽障外裔;外裔得之,足以摇动中国。”(宋李邦直《议戎策》)。这种军事价值在隋末唐初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