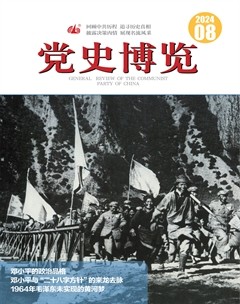白修德,本名为西奥多·H.怀特,国际知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1915年,白修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因家境贫寒,少年时期曾以在街头卖报维持生计。1934年,白修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主修汉语和中国历史。毕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前往重庆。他先是受聘于国民党宣传部担任顾问,后任《时代》周刊驻远东的首席记者。从1939年到1945年,白修德曾亲历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对处于大动乱中的中国进行了客观的报道,特别是他曾经到访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进行过交谈,对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报道,为时人和后人客观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有着罕见的自信与朝气
1944年11月,白修德搭乘飞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多重要领导人陆陆续续回到延安,使得白修德能有机会与众多的领导人相处往来和交流谈话。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白修德发现,“中共党的领袖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团体”。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充满乐观、浪漫主义精神,具有顽强坚毅的品格。经历了多年的革命战争,他们几乎变成了一家人。特别是面对日军侵扰和国民党政府的封锁,他们毫不畏惧,身上洋溢着乐观、浪漫主义精神。有时甚至还会在繁忙工作和戎马倥偬之余,去参加延安知识青年组织的交谊舞会。例如:叶剑英会带着他3岁的女儿妞妞参加舞会,无论演奏什么乐曲,“他都用跳探戈和华尔兹的潇洒自如的步法同他的舞伴在舞池里转来转去”。他们穿着厚棉衣,戴着便帽,拉着胡琴,吹着口琴,敲着鼓,在锤平了的泥土地上翩翩起舞,一直跳到深夜。白修德发现,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乐观、浪漫,而且具有顽强坚毅的品格。虽然他们曾在长达20年的斗争中遭受严重迫害,但多年的苦难没有将他们打倒,反而使他们磨炼为“韧如皮革,坚如钢铁”的战士。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具有民主平等、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国民党污蔑延安“是一种极权性的独裁专制统治”的言论,白修德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对国民党歪曲事实的行径予以了驳斥:“我在延安却找不出这种压制性机构的任何迹象,我在那里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但是其他留在那儿几个月之久的美国人,也同样找不出中共有任何像重庆那种独裁专制性的机构。”他认为,延安充满民主平等氛围,彼此之间相处轻松,毫无约束。如周恩来会邀请他的年轻的译员陈家康或者其他人在食堂打乒乓球;朱德和彭德怀会在听了对方讲的笑话后开怀大笑;即使是与外国记者交往,他们也似乎没有任何隔阂,常常像朋友一样走访美国人的住地,品尝西餐,喝茶聊天,谈笑风生。白修德说:“在延安的那几个星期是在欢笑声中度过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有着愉悦的笑容,而这背后正是延安轻松活泼气氛的显现。白修德认为共产党人之间的平等还体现在他们的领袖“从没有重庆的高级官员们的奢华生活”。即使当赫尔利到访延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时,他们没有华丽穿着,相反,毛泽东身穿一件没有烫过的肥大蓝色棉大衣,朱德身穿和普通士兵一样的橘黄色毛呢制服,周恩来身穿一件失去光泽的棕色皮外衣。他们的穿着与普通士兵和广大党员无异,身上看不到像“重庆的部长老爷与他的战栗而褴褛的书记之间的那种鸿沟”。此外,由于白修德可以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到处走访,他发现,与重庆国民政府官员相比,在延安,共产党人经常进行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如“对于一个方针的执行不当,对于无论文武当局的过错,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批评”,甚至“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他们自己的过失”,即便如此,这里却没有“重庆那种紧张的空气”,没有“重庆官员们烦恼的钩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与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白修德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有着罕见的自信与朝气。为克服严峻的经济困难,共产党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自救运动中,所有人均得参与生产来获得自己的所需,即使是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不例外。他们通过耕耘土地来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和蔬菜。中国共产党人之顽强令重庆国民政府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