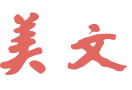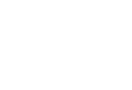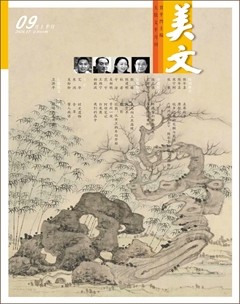一、故乡之书
峡河,是陕西70后诗人、作家陈年喜丹凤老家的一条河。“峡河西流去”,是陈年喜在《南方周末》所开的散文专栏的名字,也是他最新散文集的书名(陈年喜:《峡河西流去》,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中国的河流,绝大多数都是向东流,峡河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在陈年喜的老家,峡河经历七十里的西流之途,才折向东与丹江汇合,所以,“峡河西流去”并非虚言。
《峡河西流去》是陈年喜的第四部散文集,也是他以故乡峡河作为书名的第一本书。书名中有故乡,也有作者对逝者如斯的感叹,其中含藏着些许无可奈何,却也不乏事后的豁达——毕竟,作者是历经生死病苦,并因此而炼就了心胸的。
一如书名所示,《峡河西流去》是部故乡之书。虽然在此前出版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一地霜白》等几部散文集中,陈年喜或在零星文字中,或在个别篇章中,也曾多次写到故乡,但在《峡河西流去》中,他才以更为细密的笔触,集中书写了故乡。
在该书“自序”中,作者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这半生,和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一个是关山万里的矿山,一个是至今无力抽身的老家峡河”。他的诗歌和散文写作,也大致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其中,有些文字主要写矿山生活,有些文字主要写家乡山村的生活,许多文字则两者兼有,只是篇幅多少而已,如作者所说,两个场域“扯不断理还乱”。而其所写,有自己,更多的则是他人。因此才称得上是一部故乡之书,而不只是自我之书。
陈年喜从小到大生活在峡河边的山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根。待他长大成人,需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在贫瘠闭塞的农村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实在没办法,才外出打工——尤其是去离家不远的矿上干活。做工的地点,从离家不远的伏牛山、灵宝,到愈来愈远的长白山、鄂尔多斯、山东玲珑、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接近边境的地方。可谓天南海北,备尝苦辛。如此经历,也并非他独有,而是与他一样的一代乃至几代山村青壮劳力所共有的。仿佛共同的脚本,不同的只是细节。陈年喜的经历固然丰富、传奇,甚至不乏悲苦,与他一样外出打工的乡邻们,进而在中国大地上上亿的外出务工者们所经历的,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有人为此搭上了生命,或者牺牲了身体的一部分,导致不同程度的工伤或残疾,鲜有人能全身而退——陈年喜牺牲的则是颈椎和肺。
天南地北的打工生涯并非单纯的离家、离乡,在另一个空间场域中展开生活。毋宁说,那里没有生活,只有工作和休息间隙。对于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来说,打工生活算不得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另一头的家乡,在一家人的团聚,在日复一日的家长里短和烟火中,虽然外出打工的生活,从时间上来说远远多于在家。
也因此,他们走得再远,也不可能不回头反顾。陈年喜也一样,他心系着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次次拉扯他回到家乡:孩子出生、父母生病、乡邻去世……更不用说逢年过节,能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回家。即使平时回不了家,也要通过书信、电话与家中联系。于是,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就拉扯起更为繁复的情感牵系。
不过,虽然打工的时候常年离乡,切肤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让作者对家乡产生牧歌或乡愿式的美好想象与回忆——这是很多早年生活在农村,后来通过读书而在城市中落脚的人们常会在文字中展露的倾向,实际上也是虚假的倾向,并因其虚假而使得他们地写作变得无效。
身为农民而又不得不成为“(农)民工”的陈年喜,没有奢侈和浪漫的机会,没有对家乡产生那种乡愿式的顾念。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记得在农村时做义工、“大会战”,记得乡村生活中的质朴与狡黠、互助与计较、温情与紧张……记得几代人为什么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但他宽容、豁达,并不苛责个体,而是对过往的人与事,都抱以回望和理解的释然。(《1998年的乡村逸事》)
当然,在这释然里,也有无奈、叹息和徒然的观望。尤其是随着人口的流失,乡村无可挽回地衰败。一如农村里曾经热闹的年戏,已多年不再上演(《年戏》)。就此来说,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写作,其中相当分量,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父辈们生于斯葬于斯的乡村几十年的发展与衰落史。包括作者写到的从乡居到城镇的过渡(《村居现状忧思录》),它的复杂,以及作者对它难以割舍的眷恋:“打工生涯里,我见过数不清的野棉花,在北疆,在青海,在风沙漫天的毛乌素边缘,夏天它们是花,秋天它们是棉,但西沟岭上的野棉花,是最壮观的、最温暖的。”(《摩托记》)这些文字,可说是“月是故乡明”的当代版注释。
不过,陈年喜并没有因此而美化乡村,同样重要的是,他没有在文字中“卖惨”,而是通过清简疏朗的文字,写下略带伤感的真实记录。就此来说,陈年喜的乡村书写与此前梁鸿、黄灯等人的乡村书写一起,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尤其最近十余年以来关于乡村的新图貌,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提供了真实可信、切实可依、清朗可读的非虚构文学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