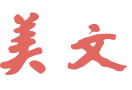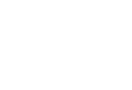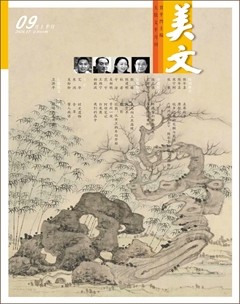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往往向东流,峡河却偏偏向西流去。只此流向,这条河流就有其不可言说的魅力。
《峡河西流去》的名字是陈年喜起的,峡河是他的家乡名,也是他家乡的河名。他打字告知我的那一刻,我眼前一亮,并对这条河流起了好奇心:倘若说百川东到海意味着融合与生,踽踽向西流则意味着什么?
2021年8月,我与陈年喜相识,经我另一位作者“为你读诗”引荐。那时,他的首部散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刚刚发行一个月,大众读者反馈迅速且热烈。
读他的文字,仿佛在听一首首每分五十节拍的广板乐曲,这个速率比我们常人的心跳还慢。我以一目十行的阅稿习惯去读,尝试多次,难以行就,因为他的文字密度是惊人的。没有故意煽情却深情,没有刻意抛撒哲思却寓意深远,真情实感和精深思虑都缱绻于他朴实平缓的叙事中。若把叙事进程比作一座山,他笔下的人、事、物,则都在以看似不急不躁的步调爬着坡,爬着爬着戛然停步,驻足在一句甚至半句话就把高潮、意外、终曲合而为一的一刻。这一叙事手法仿佛他诗歌中一个不起眼的韵脚,于他散文中却爆发震颤人心的力量。
我恍然意识到,孕育这一叙事的母体是他背负的矿山。然而,矿山绝非我们常人可轻易认知的世界,那里没有“悲欢离合”,只有“悲悲离离”。听到矿难事故导致矿工伤亡的新闻时,我们会难过,陈年喜则会悲痛。他曾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一个个鲜活的肉体粉身碎骨,化作冰冷的死亡数字。
生与死极限拉锯的场域,有文学家诞生。陈年喜是体验者,又是记录者。他看惯生死,所以可冷静地对待生死,书写生死。这也是广板乐曲适合给他的文字作背景音乐的原因,这一速率的乐曲所传达的情绪正是悲怆和炽烈。乐曲一响,一颗陨落的小星于他的笔端复活,继而再次赴死。
我爱陈年喜别具一格的文字,无论他写什么,我都愿意为他付梓出版。我们起初讨论的创作主题是“人间旅馆”,依然着眼于务工漂泊中有过交集的故事,但主题归主题,书名不可能是“人间旅馆”,因为人间太挤,市面上已有《人间词话》《人间失格》《人间告白》《人间草木》《人间食粮》《人间值得》等。
做好选题论证后,我申报上会的选题名称是“比天边还远的梦想”,这个标题出自陈年喜的诗歌《在南长河公园》,只因它给了我若隐若现的希望。选题会上,这位文学界的新星引发激烈讨论,即使推崇的人,也担忧他还有多个出版计划在排队,留给我们的是不可预知的盲目期待。
2021年9月,出版合同双签。说服大家的不是我,而是那时就已初露端倪的共识:当代散文,男看陈年喜,女看李娟。
翻看他们二人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深度生活体验者,都是以痛感书写自身与周遭的笔者,读一读就知道他们深入浅出、点到为止、巨量留白的文字张力。
约定交稿的时间是2022年3月,与其说那是一纸契约精神,不如说是一串做作的字符。我清楚,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等待他新建一个空白文档,将至少十万个字符断断续续地敲打进去,因为他的创作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漂泊二十余载的陈年喜,回到自己的故乡峡河,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荣归故里”不相关,哪怕他顶着“矿工诗人”的头衔,并已在传媒界和出版界小有名气。原因在于,故里死气沉沉,没有欢迎他的力气。
可是峡河,它细嗅到出走时健健康康的陈年喜此遭裹挟而归的满身伤痕:单耳失聪,颈椎错位,尘肺,身上各式各样的创口。它以沉默的方式重新接纳了这个游子,并以他不知情的方式慢慢为他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