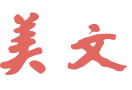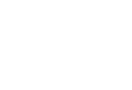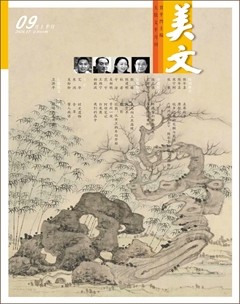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留校古籍研究所,后到校出版社做编辑。期间接触和受教于一些校内外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的先生,有四十出头的中青年学者也有年过八旬的老专家。他们学行风范各异,但都温润博雅,又极为“可爱”。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真正的“权威”或“先生”,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亲切的人。我和他们年龄、学识都相差得太多,但机缘运会,在我向学之初就遇到了这些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引入社会,领进学术殿堂。我尊他们为先生,恭敬地执弟子之礼。他们都是有着生动故事和不凡经历的大德先生。
那时候,常听他们讲课、说话。他们讲课、说话也许并不生动,但却非常精彩。他们从不依赖表情和动作,也没有什么噱头,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们的话语能力极强,用词、用语都很简单,能把一件事情讲得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绝不故作高深。有些东西,听他们一说,好像就知道了、明白了。他们才思敏捷,知识面极广且见解丰富。好些事情听他们讲过不只一遍,每回聆听,都觉得别有风致。我其实在乎的是说话的人,是谁在对我讲、对我说。树无九枝,人无十全,这些先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们是可以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亲切、平常的东西,就像邻家大爷。他们的离去,让我很难过,我知道再也没有人可以这样和我讲话了。
这些美好的过去,这些过往的先生,不仅使我回忆和遐想,更让我品味与感悟,并倍加珍惜当下的一切。人生不一定要做成点儿什么,而是要不断地去经历些什么。有些事,做了,才算不辜负此生一番际遇,和际遇中的那些先生。
黄永年:做学问重实证不讲空理论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交大迁西安,第二年被错划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安排在交大图书馆。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史事考释》《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等。
一九八四年,我毕业留校。九月开学,负责行政的周炜老师带我去见黄永年先生,黄先生说要考考我,周老师就回办公楼了。我心里紧张,对古籍整理毫无概念,不知如何应考。先生靠在书桌前的藤圈椅内,歪着脑袋、抿嘴朝我微笑。感觉在哪儿见过?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和学究。我端坐在门口的杌凳上,大脑快速运转,想回忆有关古籍整理的知识,可竟然浮现出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情报处长在江边摸大炮口,歪着脑袋坏笑的样子。他怎么长得和电影演员陈述那么像!大概见我神情诡异,黄先生用他那江阴普通话问我:中学在哪里读的?中文系都开些什么课呀,读过哪些文史方面的书啊。这时我一下轻松了,七七八八地说了我都学了哪些课程,读过什么书。黄先生边听边问,当我津津乐道诗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他皱起了眉,大不以为然。随即,便讲了过去中文系或国文系是如何讲课,要学生老老实实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怎样诗史互证解决实际问题。哦,这我还知道一些,那时文史相通,没有严格的断代界线,陈寅恪、缪钺先生都是同时应聘国文历史两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历史系。聊了一会儿,大概看我脑子也还算清楚,也读过点儿闲书,知道些史实和掌故,先生便说:现在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以后我开的课你都要来听,就叫我黄先生吧。从此我便入了黄门,跟黄先生工作、读书八年,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多年来不敢稍事懈怠,最终虽未继续从事学业,但也未曾辜负先生教诲之情。
黄先生学识广博,治学贯通文史,尤精于考辨。在中古史及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等领域被公认为大家,其他诸如古典文学、碑刻学以及诗词、书法篆刻等也都卓有建树。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套用胡适的话则是,“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黄先生自言没有“家学”,但“学有师承”。他的多位老师,吕思勉、顾颉刚,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黄先生是读其书而慕其人,对老师充满敬仰,但并不盲目崇拜,他写过不少与陈寅恪商榷或补正的文章。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文章发表后把剪报寄给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唐筼代笔作复,还附赠了陈先生刚发表在《清华学报》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黄先生总说:跟老师,主要学的是治学态度和方法。
黄先生极其聪明,兴趣范围广,欣赏境界高,做学问往往用常见史料于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且有深入研究。黄先生早年研究过先秦史,熟读前四史,《左传》更熟到大体能背诵。但他另辟蹊径做了隋唐史,晚年上溯到北朝做了点儿北齐、北周政治,一来避嫌怕人说剿袭老师,二来也避免重复。顾先生兼治历史地理、民俗学,童先生兼治陶瓷史、绘画史,而黄先生涉及书法、碑刻学,还有版本目录之学;哲嗣寿成师兄有黄先生、童先生的基因,做学问也尽量避开老先生的方向,主要做了魏晋南北朝,并继承了其父的碑刻学、目录学,也懂版本,现在是陕师大的历史教授、博导。
师母童教宁是西安市十二中的老师,童书业先生的大女儿。黄先生跟我讲,做了童先生的学生后,大概一九四八年,童先生托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先生做媒,把他的大女儿童教宁许配给黄先生。那时黄先生和师母还没见过面,因童先生说了就马上答应,但回答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便拉开抽屉翻来翻去,找出了一张指甲盖大小的师母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黄先生寄到常州给母亲看,黄先生的母亲很快也回信同意了。童先生仨闺女没有儿子,对黄先生疼爱有加,一直当儿子看待。童师母后来一直住在陕师大,我去黄先生家时,总是太师母来开门。
黄先生培养学生,要求极严,对我也一样。一入师门就让准备两个本子,以便每周交替使用,写读书札记,他要检查。第一年重点读《四库提要》,还要和其他经部、史部要籍的阅读同时进行。古人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但读《四库提要》不能代替读原典,这也是老辈学者共同的读书经验。邓广铭先生早就提出过治史的四把钥匙:目录、年代、职官、地理。顾廷龙先生也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中称“不习目录”、只知“一家之言”的人是“井底之蛙”,见到好书也会入“宝山空返”。那时的一些研究生被称为“九三学社”,即早上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先生便经常下午两点过了就去敲宿舍的门,把他们都叫起来读书了,他才到办公室工作。黄先生是懂版本、熟文献的,开有“史料学”课,很讲究文献的使用,写文章时哪些书是一手材料能引,哪些史料不能用都很有讲究。他常说,翻开一本书,只看注释的书和版本就能看出作者是不是行家。我们写文章都十分小心,不能冒傻气丢了先生的人啊。
那些年,史学领域引入西方各种理论,以改变研究方法。黄先生不以为然,他重实证,也并非不重视理论和方法。早年佩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顾颉刚古史辨派用新方法研究古史,后来也教过马列主义。先生是要求结合实际,不管什么理论,都要有史料支撑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拿理论乱套历史事实。为此,他请顺访西安的美籍华人、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教授,来讲西方史学理论,重点要强调国外也并未奉所谓“三论”为圭臬。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带汪先生去蓝旗营看辛德勇兄的藏书,聊起当年他来西安讲学,还提到黄先生让他讲美国史学界未用“三论”研究历史的往事。
黄先生喜欢与人聊天儿,聊到高兴处便问:“人都说我像演情报处长的陈述,怎么样?”歪着脑袋咧嘴笑着,“像吧。”那神气,极像天真的小孩儿!他所谓的聊天儿,是聊掌故逸闻,也品评人物、讨论问题及治学方法和选题。聊天儿便是一种教学方式,还是前辈学者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形式活泼,点化启智,无拘无束。据说当年黄侃就常带学生漫游,白天访古观今,晚上围坐喝酒聊天儿,酒喝完了,课也便上完了,学生回去睡觉,老师又接着手批一卷白文十三经。我同学宋林生的父亲是西北大学的宋汉濯教授,早年考入北大,毕业于西南联大。带的学生如费秉勋、陈华昌、贾三强等,也是如此教学。一般不在教室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而是各读各的书,各写各的文章。每学期来了谈假期的见闻和读书心得,先生加以点评,再布置些书回去读,写读书札记,有了心得来和先生汇报交流,先生则给予指导。黄先生常感叹现在的学生,达不到这种水平,这种教学方式也行不通了。
黄先生很严厉,眼里不揉沙子,做得不对的事,他看不惯一定要说、要骂!说黄先生骂人,包括陕师大一直流传的先生在教学楼关灯、关水龙头的事,都是真的。老先生经历过困难时期,看到大白天教室亮着长明灯、学生食堂门口的龙头长流水,那是一定要去关的,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老师和同学也是要训的。一九七七年国家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试用了一段儿就废止了,可学校发的文件中把副校长、副教授的“副”字还打印成“付”,办公楼里副校长门上挂的牌子仍写作“付校长”,黄先生多次找到校长办公室去批评教育他们,直到文件和门牌上不再出现废止了的简化字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