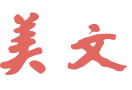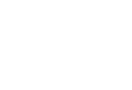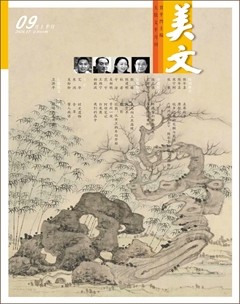一
在与地面亲密接触前,我听到体内传来“嘎吱”一声响。
那声如断竹,清脆、幽微,仅仅持续几秒。须臾间,我倒在地上,仰面朝天,左腿以一种奇异的姿势向后扭曲着,阵阵钝痛与麻木感传来,意识清醒,身体却逐渐失去对左下肢的控制。
我抬头望了望天,午后的晴空忽然变得黯淡无光。不远处,路人惊呼着向我跑来。有人慌张而又谨慎地蹲下身来察看,有人急急慌慌地掏出手机打120。
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我耳边问:“怎么样?还能站起来吗?你的家人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冷静地报出一个号码,然后静静等待120急救车的到来。
天上的云朵变幻迅疾,疼痛从遥远的身体末端传来,拖着我一点一点往深渊沉沦。此刻,灵魂与肉体已然割裂,一个我躺在那茫然失措,另一个我则努力沉心静气,让思绪脱离冷冰的地面,飘向那汹涌的云端。
我在脑子里迅速勾勒出一个名字以及一个中年男人须发怒张的样子。那人姓胡,是涟邵煤矿医院骨科的科室主任,是我的主治大夫。我们相识多年,也算是老熟人了。一方面,我信赖他如同信赖自己的亲人;另一方面却又十分惧怕他,怕到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远远地望见他的背影就躲起来或是干脆绕道走。
天知道,此刻的我是多么希望那张熟悉的大胡子脸能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我面前,解救我于急难之中。
二
半小时后,我被紧急送往熟悉的涟邵医院。在见到大胡子的那一刻,我犹如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肯放。直到此刻,我紧绷的神经才松懈下来,钻心的疼痛才真正回到身体里。
大胡子举着我的X光片在日光灯下反复查看,痛心疾首地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咋就不小心一点呢。”
顿了顿,他又安慰我:“不过放心,有我在呢。”
雪白的日光灯下,黑白胶片清晰无比,碎裂的腿骨犹如一个被摔碎的瓷娃娃般触目惊心。由于我的左腿曾经受过伤,关节不能完全弯屈,这一摔,不仅把原已愈合的腿骨生生摔折,就连原本在肉里保护着腿骨的钢板也齐齐折断开来。这一摔,其状惨烈,宛如一个人间修罗场。在全身的重量倾向身体左侧的那一瞬间,我分明听到了体内发出的金石之声。那声音如断竹碎玉般清脆悦耳又诡异至极,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一觉醒来,额上冷汗涔涔,这次才惊觉是噩梦一场。而此刻,噩梦真的重演了。
大胡子给我做了简单地处理,开完处方和检查单,便过来和我沟通接下来手术的事宜。伤成这样,施行手术是必然的。大胡子给的手术方案是开刀取出断裂的钢板,清理碎骨,对好位,再植入一根骨髓钉固定。到目前为止,常用的钢板已经不适宜用在我摔得粉碎的骨头上。这些听起来有些惊悚的画面在大胡子和我之间却仿佛是一场云淡风轻的家常对话。
大胡子还在那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解关于骨髓钉内固定术的优点和长处,我忍不住打断他:“我知道了。可以的,反正都交给你了,胡主任,请尽快帮我安排手术吧!”
大胡子说:“你以为你想做手术就能做呀,还没过血肿期呢。让你好好疼一疼,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不小心。”
话虽如此,嘴硬心软的大胡子还是给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物,马上安排上了点滴,以减轻我的痛苦。从三十岁上人生第二次摔伤入院起,我就成了大胡子的老病号,每次都是他拯救我于困苦之中,把我从横着进来治成竖着出去,又把我从一个破碎的娃娃修补还原成活蹦乱跳的女汉子,也算是竭尽心力了。而我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毫无保留地信赖他,倚仗他,好了以后却又“忘恩负义”地躲他躲得远远的。
三
手术安排在三天之后。
因为断骨没有接驳好,稍一动弹,便痛彻心腑。为了缓解血肿,伤腿必须用夹板简单固定,然后用垫子垫得高高的,一动不动地牵拉在床头,像极了上刑架。慢慢地,钝痛逐渐演变为胀痛、钻痛、刺痛,痛得让人分不清白天黑夜。好在大胡子开了消炎止痛的药,这才顺利熬过手术前三天。
临进手术室前,几名医生和护士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我挪到推车上。
电梯门开了,我静静地躺在推车上,等待命运的又一次裁判。随着厚厚的手术室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我的心也无所依傍,跌入了未知的深渊。
时隔几年,我再次躺在无影灯下。几名身着蓝大褂的医生护士正忙着做术前准备。手术室冷气开得很足,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我竭力咬住牙齿,不让它发出声音。这时,一位护士发现了我的异状,赶紧拿来一条床单替我盖好。手术床边,冰冷的仪器滴滴响着。刀子剪子钳子在器械盘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名男手术麻醉师正与护士们低声说笑着。这样的骨折手术对于他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大概一天要做好几台,他们似乎忘了正躺在手术床上的我。眼前这一切分明是因我而起,却似乎与我无关,我孤独而又无助地躺在那,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
终于,麻醉师结束了与女护士们的说笑,捏着针管向我走来。
“能侧躺过去吗?对,就这样,把身体尽量侧过去一点,待会会有点胀痛,千万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