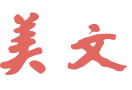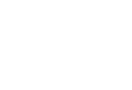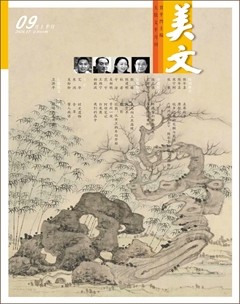夜 影
少时,家在一个狭长的院落里,院子尽头,有一间瓦房,我们叫它“上房屋”,上房屋里先后住过两位独居老人,一女一男。女的亡故后,男的搬进来,没多久,也去世了。院里一个大伯跟邻居们扯闲话,说看见上房屋的墙上,老太婆伏在老头背上,木偶戏般一揣一揣地动……邻居戏谑他,说这货肯定又喝上路了,大家显然没把他的话当真,而我却惊立了好久,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靠近上房屋,怕那团黑色的影子出现,连上厕所也是舍近求远地跑到外面。厕所入口在上房屋左侧,如厕要通过一个狭长的过道,有一晚,稀饭喝多了,撑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上房屋走近,月光很明,洒在地上有一股寒朔之气,我脑子里闪现出老太太龙须酥一样绞缠的白发,敞着门,端坐在屋中央,目光里带着霉变的菌丝,整个人发散着枯朽的气息,她唯一一次开口,是我家砌了灶台,阻挡了她的视线,她发了很大的火,把拐杖捣在地上,后来我母亲说,她看不见我们做什么饭,怕做好吃的不让她一口……在我快接近厕所过道口的时候,听见了一声叹息,我几乎是以我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奔回屋里,别上门栓,再也不敢出去。我把废弃的一个痰盂放到屋里,权做我的便桶。
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那个大伯,那黑影是真的吗?他似乎已经忘了这茬,因为他每天都要说上大量真假参半的话,他说,啥?我听不懂,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上房屋老头老太太的影子为啥要合在一起?大伯笑笑,他俩是两口子啊!
那时我已经知道了两口子的确切含义,比如我的父母,我姥爷和我姥娘,可是我又疑惑了,既然两口子,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而要各自孤绝地走向生命尽头?虽然对于大伯的话我不再笃信不疑,但因为那个影子在我心里盘踞太久,它的杀伤力早已超越我能承载的负荷。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们一家搬进装修一新的上房屋,我还是能隐隐感到一股森凉之气。
我的父母虽然没像老头老太太一样分离,但不睦的阴云常常笼罩,口角和厮打更是家常便饭,我那时常常盼望他们分开,像老头老太太一样各自生活,我自然是要跟着母亲的,每当我父亲脚步趔趄地投影在上房屋时,我的恐惧和不安不啻于那团传说中的鬼影。那时我觉得这世上最不靠谱的事莫过于跟父亲一起生活。他通情达理,又蛮横暴躁,开明达观,又偏执绝望,他对街头衣衫褴褛的乞丐慷慨解囊,却对叫卖声过大的商贩当面咒骂,他对我亲近姥娘家的人报之以充分理解,但有时又陷入悲身世恨出身的怅惘中,且他的情绪经常无端陷入某种不平和悒郁,好像他是全世界的弃儿,我们理应贴补他一个公道。
其实真正欠他公道的,也许只有我奶奶一人。
他提起我奶奶,表情常常恨恨,说她烧了他辛辛苦苦攒钱买的笔和纸,断了他做画家的梦,并且饿他、冻他、骂他、打他,兄弟姊妹间就他最惨。这些能宣之于口的恨我们都反复闻听,还有一部分,关乎一个家族的尊严和脸面,父亲哪怕再醉,也不曾在妻女面前怨怼过这一层,我也是在多年后才知晓,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在那个拘谨封闭的年代里,行为为村人诟病。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我父亲的婚事,没有人愿意嫁到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里去。甚至邻村的人,也当着我父亲的面指指戳戳。贫穷、不公、屈辱反复折磨他的心,他从未被善待,情感的旷野土质瘠薄,实在没有更生爱的养分和能量。对于他自己的孩子缘于那份天然的血缘和纽带,他在清醒且顺心的时候,是一个父爱泛滥的人,他用最肉麻的昵称呼唤我们,用胡茬扎我们的脸,跟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可是一旦被外界的人和事叮咬一下,他就变成了一个易感且暴怒的人。
他心情大好的时候,带我和弟弟去北关河边玩,没泳衣和救生圈,我们就穿着夏天的短衣短裤下水,在清浅的河里戏水,我父亲看着满目碧波和亲儿的笑脸,眼神泛光,这一幕又勾起了他骨子里的浪漫因子,但这种艺术家似的情绪化和小县城的气质背离相冲。那时的北关河岸上是一所医院,因为毗邻北关河,所以大家都叫它北关医院,河岸上有一处弃壤,久而久之成了倾倒医学垃圾的地方,听说常常有人一个趔趄,被一个胎儿的颅骨绊倒,鉴于如此骇人听闻的传说,我几乎从不去踏足那片土地,我的父亲却说,要去那里走走,我和弟弟留在原地。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原来在我弟弟之前,我母亲曾流掉了一个孩子,已是颇具人形的一个女胎,被引产了,当时都是家属负责去丢弃这些弃婴死胎,我父亲说,扔掉她的时候,她还在我的手里微颤,我父亲丝毫不觉得跟孩子们说这些有何不妥,他眼里噙泪,神色黯然。可是这种情绪很快在他朋友们攒成的酒局里冲淡消弥。他无比受用地沉浸到神侃胡吹和吃香喝辣中去了。
租 客
在电影院泡大的小孩,想象时画面感很强,还自带音效和配乐。真正让我想象力飞速发展的,还是书。有一天下午,我在舅舅家发现了一本《一千零一夜》,那时我识字还不多,但意思已经能看懂,一整个下午,我都沉浸在文字建构的奇异世界里,坐在门槛上石化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