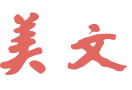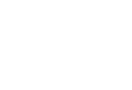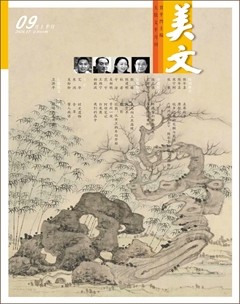雨落草原空
从红原醒来,轻盈的雨,落在窗外无垠的草原上,一片苍茫。
摸黑来到红原时,星光下的草原,早已进入梦乡。我们在县城与草原的边界线附近,随意找了一家旅店住下,说好次日清晨早起看草原升红日的盛景。谁承想,满天的星光里竟藏着几朵不安分的乌云,它们于夜深人静时分悄然结成了联盟,要在黎明抵达之前酝酿一片云雨。
心里不免生出几分失落。
不能在草原与朝霞构筑的梦里醒来也就罢了,还要和潜意识里天高云淡的草原擦肩而过,雨中的凉意就一阵阵涌上心头。在丘区简阳长大的我,从没有真实地置身过草原,电视和网络上的构图,诗词和歌曲里的吟唱,构成了我对草原的全部想象。天该是蓝的,云该是淡的,草该是青的,牛羊该是散淡的,牧人该是奔放的,从未想过清新明丽的草原闯入一阵朦胧烟雨,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按计划,我们要在红原县城周边的草原上牛羊作伴、骑马驰骋,感受天地的辽远与历史的壮阔。这一场雨半点要停的意思也没有,我们只好把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日程提前。然而有些醉心的风景,有些难忘的故事,总是在计划之外,闯进我们的生命。
公路在广袤的草原伸向远方,好似在宣纸上拉了长长一笔,那青青的草原就是大片的留白,那若有似无的烟雨就是淡淡的墨痕,简单几笔的泼墨画境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驱车在雨雾笼罩的草原上,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字来——“空”。空空如也的“空”,空山不见人的“空”。没有流动风景的草原是空的,成群结队的牛羊在低洼处躲雨,牧民也回到帐篷喝起了青稞酒,只有那些雨滴不停地敲打着车窗。心仿佛也是空的。妻子把头靠在车门上打起了盹,而我则懒心无常地踩着油门、听着老歌,只有女儿伊伊不停地擦着车窗上的雾气,好奇地打量着窗外的一切。
苏轼写过一种“空”,是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空”。在他的眼里,“水光潋滟”是极致之美,“山色空蒙”也别有一番韵味,反倒成全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绝唱。生长在阿坝的藏族作家阿来也写过一种“空”,是长篇小说《空山》里的“空”,是古老村落在历史山谷中久久回荡的“空”。在伊伊的世界里,这草原的“空”,是否也是水墨晕染开来的幽远古意,亦或是历史长河响起的文明回声呢?年仅三岁的伊伊没有过多的联想,也没有落入俗套的标准审美,只在幼小的心灵上一遍遍着上烟雨草原的原始底色。
或许,此时此景的草原,将成为一种干净而纯粹的意识,潜藏在脑海,交汇在血液,成为伊伊一生的诗意源泉。
雨渐渐小了,风在草原上吹着。慢慢有牛羊闯入我们的视线,有的埋头吃草,有的低头喝水,有的打量远方,有的成群迁徙。“快看,羊群!”妻子从睡梦中醒来,惺忪的双眼瞬间充满神光,不停地搜索着羊群的踪迹。空空的草原,终于有了一些流动的风景,这让人瞬间来了精神,飘荡在车内的旋律似乎也悠扬起来。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伊伊突然背诵出北朝的民歌时,我猛地一怔——年幼的伊伊,背诵过《敕勒歌》,但歌中景、词中意未必能深刻领会,那么她是怎样做到见景生情的,又是怎样做到精准抒发的呢?
我从后视镜分明看到妻子的脸上难掩激动,紧紧地把伊伊抱在怀中,不停地抚摸她的头发,亲吻她的脸颊。我甚至看到妻子的眼中。有些热泪在打转,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温度。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情感联系,有时用不着过多地诠释与解读,它往往在岁月沉淀抵达之前最自然地流露在某个美好的瞬间,最终定格成人生最可贵最恒久的记忆。
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天真慢慢被侵蚀,感知渐渐被风化,往往偏执地认为最好的风景是外化的内心,而非内化的山川。面对雨中的草原,我和妻子发现、感知和抒发美的功能,都远不如伊伊,似乎我们早已失去了欣赏“空山新雨后”“清泉石上流”的那份闲适与恬淡,难以抖落身上的尘埃。
日常里,妻子喜欢摆弄花草,刚开始在阳台上放了几盆君子兰、红掌、绿萝,错落有致,十分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