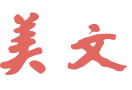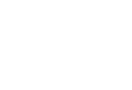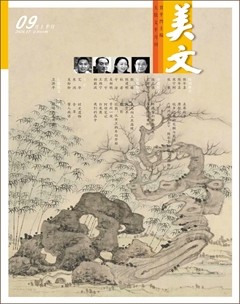呲的一声,火柴划燃,一双手捧着火苗移向一根烟。但烟躲开了,叼烟的嘴吹灭火苗,黑暗中有话冒出来:
“先给艾华点。”
呲一声,火柴又划燃了,火苗凑过来。我把烟塞到嘴里,对准火苗吸燃,忍不住咳嗽起来。
“Sorry!惭愧!”
火苗晃熄。我已咳完,闻到一丝松木的清香,吸吸鼻子,烟草和火药的味道有浓有淡。
“鼻子通了吧?”
“通了。”
1979年,小镇夏夜,是一支烟治好了我的感冒。我第一次抽烟,给我烟的是“长发彭健”。给我点烟的是彭春,大我一岁。彭春喜欢把刚学的英文挂嘴上,紧接中文,比如“Sorry”加“惭愧”,比如“Spring 彭”。夏天了,彭春又突然给自己改了名:
“夏季我就叫Summer 彭。”
抽完烟,三人走到变压器围墙边,都抬头看电杆上的路灯,看赴火的飞蛾。看得无聊了,就跟往常一样翻进围墙,单腿落地,是为了防备变压器有电漏至地面。我歇口气,然后单腿顺时针跳半圈,扶着墙听一会儿变压器的噪音。
“嗡嗡嗡的。”唐西兮每次都说,“好多蜜蜂!”
她的声音被蜂鸣吞没,再也不会响起。彭春跟我一样听一会儿,迅速换条腿,顺时针再跳半圈。彭健这回没有扶墙,也没有换腿,一口气跳完一圈,翻墙出去了。
等我最后一个翻出来,三人就坐在围墙的阴影里,屁股下是周瞎子摆摊用的砖头,多出的一块从前是属于唐西兮的。
春天变成夏天,唐西兮回到童话里去了。镇上的人再也看不到她踮脚走路,也看不到她坐在彭健的单车上。她不是坐三角架横杠,就是反身坐后座,坐姿叫人看不顺眼,后来慢慢看习惯了,也就习惯了。如果她在后座上平伸双臂,彭健脱离车把的双手也平伸开来,两人的滑翔便能赢得喝彩。
“比翼双飞!”彭春说。
“南方有比翼鸟焉。”周瞎子背书,“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
彭春从周瞎子那儿听说“鹣鹣”,就教彭健和唐西兮更准确地“比翼”:一人只伸一只胳膊,两人在单车上试试,成功了。一人只睁一只眼、只站一条腿,两人在地上试试,也成功了。从此形影不离的两人一出现,彭春就大叫:
“鹣鹣来啦!”
“鹣鹣”少了一半,剩在镇上的彭健孤单了。他不再骑单车,白天也不大出门。深夜,如果有手电筒从西街往东街晃过来,那束光最后一定会照亮镇上唯一的邮筒。
天热了,我喜欢在夜里游荡,几次碰上彭健。两只手电筒打打招呼,两个夜游神渐渐亲近。
“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
周瞎子的书真是背不完。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彭健和唐西兮“比翼”是好看的,特别是一人只伸一只胳膊的时候,彭健和我“连臂”则是怪胎,跟勾肩搭背一样,并不好看。白天在学校内外常常见到勾肩搭背的人,我和彭春学了学,别扭。晚上,彭健也曾试图跟我勾肩搭背,被我拒绝了。还是像神话里的夜游神一样,进化成单个的人,独立行动比较好。两只手电筒在夜里遇上了,可结伴,终分手,一个人走的夜路才是真正的夜路。
两只手电筒都是虎头牌,Tiger Head Brand,Made in China,这两句英文彭健读得比我利索,我心生佩服,佩服他的手电筒是三节电池的,我的只有两节。
跟彭健熟了,我也没有更多了解唐西兮,只认定她跟彭健一样,确实是当过运动员的:彭健是乒乓球运动员,她是羽毛球运动员。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记起唐西兮哼唱的歌,是当时流行的《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原来从她嘴里出来,并不是随意的。
“我给她的信里,总会夹根羽毛。”彭健的深情已是痴情。
恍若昨天,恍若昨天的昨天,彭健喜欢回忆唐西兮在镇上度过的日子。晚上关了灯,彭健会让唐西兮打开手电筒,两人一起玩手影。在手电筒投射的光线中,彭健的两只手巧妙造型,蚊帐上便会出现一个吼叫的虎头。虎头上有胡须,由几缕长头发映射出来。是彭健自己的长头发,某次被教练强行剪掉,彭健保留下来的。彭健的运动员生涯过早结束,据说与他不肯按规定剪去长发有关。
“科恩!”彭健说,“我十岁进体校,看到科恩留的就是长头发!”
“科恩是谁?”我问。
“Glen Cowan,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一九七一年来过中国。”彭健说,“一九七一年到今年,八年了……”
“你见过?”
“没有,画报上看见的。是个左撇子。长头发,戴帽子,帽檐也长。”
从体校学生到专业运动员,从县里到省里,彭健在外面打了八年球,最后还是回到了镇上。失学加失业,其中的缘由恐怕不只是长头发。有传言说他犯了政治错误,他并不忌讳:
“是的!我反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