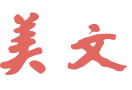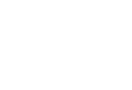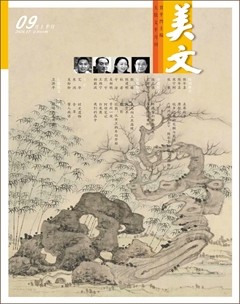我的高中是在斗门中学上的。斗门中学名声很响,斗门、镐京、纪杨三个公社,只有斗门中学设有高中,况且一个年级只有三个班,相当于一个公社只有一个班。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期高中生,生源中既有应届初中生,也有往届初中生,年龄差距大,能考上高中的真称得上是烧了高香,又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地叫,大家都很珍惜,学习十分下苦。毕业二十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张罗一个年级三个班的同学搞了次聚会,邀请来的班主任和化学、物理老师都说:“在我们教过的学生中,你们这届是最用功的!”还说:“老师们聚到一起常谈起你们,为曾经带过你们而高兴。”如今,提起在斗门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同学们仍然记忆犹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
小学是怎么上过来的,我记忆不是很清晰了,只记得夏天光着脚板,冬天抱个土碗样的小火炉。夏天脚被枣刺扎个口子,冬天手背冻得像个馒头,那是常事。不管生病还是磕伤,没有误过课。加减乘除和算盘,口诀背得滚瓜烂熟,算数也快;语文凡是课本上的字,都会认会写,小人书能看懂,《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大书,能半懂半不懂地看完。父辈们多数不识字,我上五年级时,队长何伯就让我帮会计记工分、写标语、办黑板报。“俺娃好好念书,长大了干大事,不要像我和你爸一样一辈子打牛后半截。”这是父辈们常说的话。
下决心好好念书,却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上得跑跑颠颠、断断续续。还会不会有高中?能不能上成高中?心里向往着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
一天中午,太阳当头,晴空万里,站在河岸能清楚地看见南山。我挽着裤腿光着脚,正在苞谷地浇水,忽听有人扯着嗓子喊我。走出苞谷地,一看是村支书。我们村大,支书家在西堡子,我家在东堡子。支书比我爸还大几岁,我叫他伯,见了面很尊敬他但平时没啥来往。疑惑间,他问我:“娃,想上学不?”我愣怔中又惊又喜:“想!”又疑惑地问:“上啥学?”“上高中,在斗门中学。”支书随身揣着介绍信,让我填写,然后替我看水,叫我蹬上他的自行车,赶紧去报名。泥里吧叽到了学校,登记的老师说,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原来很有限的名额分配到各村,要由大队推荐;我们大队几个干部商量完,支书找我找了好半天。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一定要亲自见到我,当面问一下和叮咛一声才放心。
登记的老师说:“回去好好准备一下,要考试的。”
等了没几天,接到考试通知。数学试卷我完全是蒙的。因为不是本届初中毕业,又已经劳动两年,试卷上的题都没学过,到底做得对不对,得了多少分?一直也不知道。语文没别的题,就是写篇不少于八百字的作文。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题目叫做《记一位老贫农》。我们村老贫农多,我家也是贫农,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好写。我以当贫协主席的四伯为原型,做外貌和性格描写,串联了发生在村里不同人身上的几件模范事例,笔不离纸,唰唰唰写个不停。监考老师在教室轻轻转了一圈,从我考桌旁经过时,逗留片刻,看了看我的试卷,走到讲台边回过身,轻言细语地说:“同学们一定要想好了再写,不要跑题,不要闷着头只顾往下写!”他话语柔和亲切,声音与常人不大一样,像是从喉咙底部发出来的。他是在提醒所有考生,但在我看来,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写完作文,未见时间到,又仔细改了一遍。入学后才知道,这位监考老师是给我们教俄语的杨老师。
二
放榜那天,早早跑到学校,只见校门口围的人不少。大红榜贴在墙面上,从左往右看,最后面一张红纸黑字有我名字,心甜得像吃了块糖。回家告知父母,父母眉开眼笑,那天特意割了一斤肉做了顿臊子面。
上高中是要住校的,还转户口。爸为我张罗学费和在学校搭伙的口粮,出门进门哼着秦腔;母亲为我拆洗被褥,缝补换洗衣裳,还特意织了一截蓝格子布给我做了两件格子衫,灯影里飘荡着她哼唱《绣金匾》的曲儿。到学校报到那天,我自行车一边驮着我和一位女同学的被褥。她住我家斜对面,辈分高,虽同龄但我却以姑称呼。她的被子是大花被面,不知被自行车哪儿擦破了一个洞。到校交给她时,她笑着说“没啥没啥”,但听其他女同学说,背过人她心疼得落过几次泪。
斗门、镐京、纪杨三个公社,都是平展展的大地方、好地方,是长安的“白菜心”。斗门偏西南,往南是细柳,往西挨沣河;镐京在东面,挨着鱼化寨,离城最近;纪杨偏西北,往北是三桥,往西是咸阳。这么三大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跨度五年,不知有多少适龄考生?可只有一所学校三个高中班!斗门中学就在斗门镇。准确点说,不在镇子正街上,而是在镇子东边,离西安到余下的铁道不远。余下是军工重镇,又有个电厂,所以修了一条铁路专线,现在这条铁路还用着。学校西边是场地很大的斗门粮食收购站,夏秋两季,人和马车、架子车的队伍排着长龙交粮食,也交白花花的籽棉。校园宽敞,除了一排排教室和宿舍,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
斗门中学是1955年建校的,但一直只有初中;我们这批学生,是建校史上首届高中生。报到这天,校园悬挂标语,老师热情迎接,同学们喜气洋洋互相介绍。到底是大学校,教室、窗户、桌椅板凳都比村上的学校阔气,连黑板都要方正、黑亮一些。我们班五十六个同学,男生占三分之二,女生有三分之一。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刘。她早早在教室招呼我们,与每个人对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