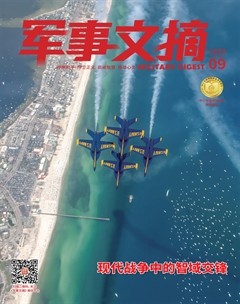路透社近期发布一项独立调查,证实美军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为了遏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了“反中国疫苗”的隐蔽宣传行动。时任美太平洋陆军特种作战部指挥官乔纳森·布拉加少将牵头负责,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具体实施,操控数百个虚假账号散布伪造信息,煽动仇华情绪,造成严重后果。这是继2022年斯坦福网络观察室曝光美军长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推特、脸书、照片墙、元宇宙等社交媒体平台,对中亚、中东、伊朗、阿富汗等地网民实施隐蔽宣传后的又一重大事件。美军阴谋屡屡见报,表明在网络域利用机器操纵、深度伪造、巨魔农场等智能手段开展隐蔽宣传行动已成为一种独立作战样式,被美军熟练运用,对国际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挑战。
驱动美军隐蔽宣传行动变革的关键性因素
数智时代,互联网的隐蔽性和非归属性为隐蔽宣传行动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通道,在以下因素的共同驱动下,美军在网络域主动作为、大胆进攻。
内在动因:自身难以抑制的霸权战略需求 利用宣传手段瓦解敌军战斗意志、冲击民众抵抗精神、干扰外界认知能力,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是美军一以贯之的宣传策略。在互联网技术方兴未艾之时,美军便开始秘密操控网络媒体来配合其战场行动:科索沃战争中,建立多个网站污蔑南联盟军实施“种族灭绝”行为,蒙骗国际社会,为其入侵行为洗白;伊拉克战争中,动用各种网络传播手段影响战时舆论环境;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政权进行妖魔化宣传,激发国际社会愤怒。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平台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兴起,网民舆论逐渐成为能挑战官方话语权的强大力量。美军深切地感受到,夺取网络空间舆论话语权,对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利益至关重要。鉴于美军负面形象较多,目标国民众对美军官方发布的信息普遍持有抵触或怀疑态度,公开宣传效果往往欠佳,但隐蔽宣传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创设虚假账号,以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智库或者普通民众的身份发声,更具亲和力,更能赢得受众信任。美军能够不显山露水、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进行深度洗脑,宣扬美军“正面形象”,掩盖“不和谐的声音”,谈论官方无法触及的“敏感议题”,无需顾及被揭穿后导致的责任追究、公信力下降和声誉受损等问题。
外部动因:大国竞争激发网络域博弈升级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坦言,“媒体被美国的敌人玩弄”是一件令他睡不着觉的事情。美军认为,“伊斯兰国”“伊朗网军”“叙利亚电子军”“黎巴嫩真主党”“俄罗斯网络部队”等敌对力量,非常擅于利用网络进行秘密宣传。近年来,美俄之间的认知对抗愈发激烈,美方声称俄方构建了以“政府机构/官方媒体、国家幕后资助的全球传播媒介、代理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虚假信息”为支柱的虚假宣传生态系统,传播政治谣言、鼓噪虚假新闻,助其在与美西方战略博弈时赢得先机。对手持续升级的网络宣传能力给美军带来巨大不安,恢复美国在冷战期间对竞争对手实施的侵略性隐蔽宣传行动的呼声在美军内部越来越高。相较于实施隐蔽宣传行动,发起公开网络对抗的性价比较低,例如攻击对手的网络基础设施或网络资源,仅能收获短期效益,对手的网络传播能力可以迅速恢复,但美军却要付出较大代价,比如国内外舆论压力、对手的猛烈报复。而在网络域开展隐蔽宣传,可以长期不间断地进行,阻止敌对势力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以极小代价收获重大战略利益,同时掩藏美军参与痕迹,即便行动失败也能合理推诿。

技术动因:人工智能促动社交网络武器化 新媒体革命的蓬勃兴起、互联网技术的更迭升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跃迁,为美军隐蔽宣传行动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契机。美军联合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研发了一系列人工智能项目,全方位掌握目标受众的语言文化、关注焦点、情感偏好、网络行为习惯等要素,确保“定制”内容能够更好地被传播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