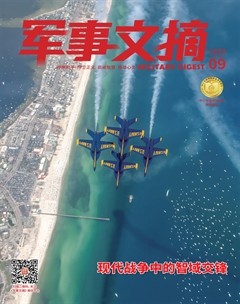“认知域”首次出现于2001年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网络中心战》报告中,与“物理域”“信息域”一同构成信息作战的三大空间。概念提出初期,美军认知域作战能力主要强调军事信息和决策优势,涵盖范围未扩展至社会公众。随着大国博弈逐渐深入,美军认知域作战能力构成外溢效应明显。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ACT)推出的认知战系列项目文本中,将公众舆论“武器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并提出脑科学“军事化”的新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认知域作战能力成为美国改变大国间综合实力对比的新突破口。其本质是以美军为核心,协调各方资源,集成跨学科技术,操纵目标群体的认知机制,以削弱、渗透、影响甚至征服或摧毁对手的非对称能力。其构成呈现军地联合、盟友结合、多域融合的新特点,大国竞争指向更为突出,灰色地带竞争的属性更加明显。其向前发展过程中不断继承战略传播、隐蔽行动、文化渗透等既有优势,还持续吸收深度伪造、生成式大模型、神经控制等新兴技术。从研究作战能力构成的角度出发,可厘清其认知域作战现阶段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新兴领域与强敌竞争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基础——传统战略传播能力
根据美军联合出版物1-02号《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战略传播是了解和接触关键目标群体的活动,为作战行动和美国利益提供更好的舆论环境。作为美军认知域作战能力的传统组成,战略传播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20余年,现在仍是美军塑造对外形象、控制公众舆论、改变政治影响的主要手段,其实践进程主要涵盖三个方面指向。

巩固友好群体。在国家层面的战略传播中,公开政策宣示、正式场合发声、传统媒体宣传是其向国外受众传播美式价值观和战争逻辑的主要形式。一是精准定位目标人群。在发动对外战争前,美军一般会筛选目标国内的亲美“基本盘”,大打“人道主义干涉牌”来巩固有利于己的意识形态氛围。二是积极扩大影响力。以声援、资助、扶植等手段不断提高亲美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利用该群体为美军具体作战行动站台发声,提高军事行动的政治效果。三是固化形成机制。从奥巴马时期开始,利用目标国中友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和有影响力个人,已成为对外舆论引导的“三要素”。在此背景下,巩固全世界“亲美”分子阵营是美军进行战略传播的固定动作。
拉拢中立群体。在战略传播的视角下,中立群体数量占比最大,其认知是决定美式观念输出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一是推行“零距离”接触,确保覆盖。由于美军的全球部署模式,使用当地语言建立新闻网站、进行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与当地民众进行面对面善意接触是其部门层面战略传播规定的重要原则,不同层级群体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有效覆盖。二是善用“灰色宣传”,降低负面影响。在20世纪末的几场战争中,美军利用灰色宣传手段掩盖自身侵略行径,以“民主自由”概念对当地民众进行洗脑式宣传,采取偷换概念的方式对符合美国利益的观点进行隐蔽推销,从而不断达成观念占领和“思想殖民”的效果。三是打造靶标效应提升效果。美军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中,对相关地区的族长、头目等关键人物持续投入资源,企图以重点人物观点的改变带动不明真相群体舆论的转向。
扰乱敌对群体。美国防部的《战略传播报告》强调,信息作战是干扰、篡改、毁坏敌人施加非物质影响力的关键。一方面,常见的心理战、军事欺骗、隐蔽行动、扶植代理人等都是美军在正面战场制造恐慌、离间对手、震慑进攻的基本手段,其中对目标国国内军政要员、作战部队、支撑单位等关键要素的心理攻势和舆论压制,能保证其在发起行动前就具备非对称的战场优势。另一方面,持续的抹黑和污蔑使得此类战区层面的战略传播可以不断削弱对手国内的民众信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