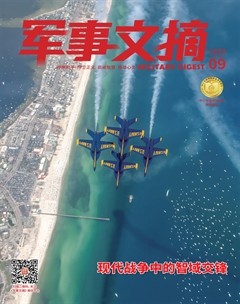近年来,新兴军事学说如“认知战”“复原力”“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等纷纷将平民纳入战略考量,强调平民和民事部门在武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趋势的根源在于平民日益广泛地介入武装冲突,使得“平民化”成为各国和各地区武装冲突的共同趋势。
西方经典军事理论主张平民是战争的受害者,应受到特别保护,并强调军人与平民之间的明确区分。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国家垄断武力”原则在军事学界的体现和延伸。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深刻改变了战争形势,也为平民介入武装冲突奠定了基础,“国家垄断武力”原则由此走向瓦解。从宏观层面来看,战争与和平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这种模糊性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军人”与“平民”身份界限的逐渐淡化。
平民介入武装冲突的深度、广度难以定性分析,因此本文选择对平民参与武装冲突渠道进行定性分析。包括军队文职雇员、私营军事安保公司雇员与种族/宗教武装组织民兵,以及将平民视为作战对象的认知战理论。
“国家垄断武力”原则的产生与外延
在西方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仅有国家能够合法使用武力”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原则被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广泛接受,马克思·韦伯将其阐述为“国家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它(成功地)声称在特定领土内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即“国家垄断武力”原则。“国家对武力的成功垄断”也被视为与封建国家相区别的现代国家的决定性特征之一。

“国家垄断武力”原则是对一系列社会契约的总结,在该原则的基础上延伸出 “战争状态”“战斗员(军人)”“非战斗员(平民)”等概念。军人与平民被严格区分,保护平民免遭武力侵害的交战规则与道德规范最终以国际人道法的形式得到固定,而对平民的特别保护同时意味着平民与武装冲突的明确分割。
不过,“国家垄断武力”原则并未被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接受:该原则及其衍生的“平民与武装冲突的分割”根植于“西方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西欧以外的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没有经历类似的历史时期,在部分地区,“国家垄断武力”不被公众认可;相反,种族、教派、宗族、部落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保留武力、对抗中央政府的行为广泛存在,且被认为合法。
最终动摇“国家垄断武力”原则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安全形势的显著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军事革命的兴起,以及民粹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回潮。在接受“国家垄断武力”原则的国家或地区,新军事革命为文职雇员、信息战/认知战理论、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不接受“国家垄断武力”原则的国家或地区,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回潮使得种族、教派矛盾更易激化为武装冲突,并广泛吸纳平民参与种族/教派民兵组织。总体来看,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使“平民介入武装冲突”成为覆盖各国、各地区武装冲突的共同趋势。
武装冲突“平民化”的表现与驱动因素
武装冲突“平民化”在不同类型国家中拥有不同表现形式:在军事实力较强/中央政府强势的国家,武装冲突“平民化”表现为文职雇员、信息战/认知战、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军事实力较弱/中央政府弱势的国家,武装冲突“平民化”表现为效忠种族、教派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组织。虽然武装冲突“平民化”在军事实力较强/中央政府强势的国家与军事实力较弱/中央政府弱势的国家间表现迥异,但由于大国干涉、区域冲突影响外溢、全球危机扩散等因素,“平民化”在单次武装冲突中可能同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军队信息化强化文职雇员作用。管理军队作战指挥系统、武器装备系统、通信系统的军队文职雇员已成为现代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度职业化的象征之一。文职雇员在全球主要军事力量中的日趋活跃是平民深度介入军事活动的标志之一,这一趋向可追溯至美国发动的“第二次抵消战略”。
越南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美国军事力量衰退,1968年至1975年,美军四大军种现役兵力裁撤幅度均在30%到50%间,总人数从350余万人削减至210余万人,同时由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北约常规军事力量与核力量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全面反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