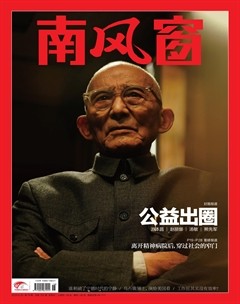直到两岁,乐乐还是不会说话。他的妈妈甘洁抱着“贵人语迟”的期望等待了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去儿科医院找最权威的专家,得到了孩子被确诊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结果。
ASD为很多现象提供了解释。
比如,乐乐对人的关注度不高,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唱歌挥手的时候,他自顾自地滑滑梯。但最为显著的表现还是,乐乐不说话。叫他的小名,他不应,想喝水,想上厕所,他也不表达。
小孩不言语,会让妈妈变得自卑。刚开始,带乐乐在小区散心的时候,甘洁会让他和其他小朋友互动,挥挥手说再见之类的,但尽量不让孩子们在一块儿待太长时间,“握个手就分开了”。她说,作为一个妈妈,她还是有很多的不甘。
立夏前后,乐乐满三岁,甘洁决心要对孩子进行言语干预。她最终前往一家名叫“儿语工坊”的机构,成为徘徊在这里的众多家长之中的一员。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社会企业,脱胎于一群“95后”年轻人在大学期间的公益实践。他们从关注唇腭裂孩子发声不清的问题开始,逐渐接触到越来越多受困于“说话”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小孩,也偶有成年人。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说话”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小事。但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件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事情,一群年轻人,磕磕绊绊地走过了八年。
暴雪
安安刚把儿子小满送去幼儿园一个月,就听校车跟车阿姨讲,“你这个小孩可能说话不清楚”。她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校车阿姨专门负责接送这么多同龄的孩子,应该不会凭空论断。在此之前,小满超过两岁都没有说话,大家都以为是男孩发育较晚。
她自称是那种“杀伐决断”的母亲。在全职投入育儿之前,她是职场中领导“优秀团队”的“优秀经理”,一年12个月能拿13座奖杯,在养孩子上也延续了超强的执行能力。为了解决小满说话的问题,她花了一整个月在网上做调研,最后给儿语工坊打去电话,预约了测评,测评当天就决定开始上课干预。
她至今仍然记得通话那天,是周二,“我打得很不巧”,周二周三都是这家语言干预机构的休息日。等待的两天时间,每分每秒都变得很漫长。那时候,小满会把“哥哥”说成“dēdē”,把“汽车”说成“qùhē”。她说:“这件事情(语言干预)不等同于任何事情,这就是我头等大事,任何事情都不要妨碍我去干这件事情。”
孩子说话不清楚,对于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安安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走丢了,哪怕找到警察,都说不清楚电话号码。
预约测评的周四,是12月里一个零下6度的暴雪天。“多冷哦。”她说。40多分钟的测评结束以后,安安听老师讲,测试的21个拼音中,小满错了16个。
从专业层面讲,小满的情况被称为“功能性构音障碍”,这意味着他的构音器官形态和运动功能无异常,听力也正常,但将发音错误作为固定状态,并且找不到明显成因。
在儿语工坊的门店外,聚集着各式各样受困于“说话”的孩子,包括ASD患儿、唇腭裂患儿、聋儿、语迟的孩子等。安安发现,到了周末,工坊会出现很多“拉杆箱”,来自外地的家长们会趁着放假带孩子来上课,甚至有家长在周围租房做干预。
如安安所说,“任何东西都要靠嘴去表达”,无法清楚准确地说话,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四岁的孩子还没有开始社会化,但五六岁的孩子如果说话不清,就会感受到自己疏离于人群,因而变得性格自卑和内向。年龄越大,人们受说话能力的影响越大。
孩子说话不清楚,对于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安安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走丢了,哪怕找到警察,都说不清楚电话号码。
儿语工坊的团队成员脸脸记得,三年前,她曾给一个17岁的女孩上课。女孩的妈妈很早就发现了孩子说话清晰度低的问题,但女孩不愿意做干预;直到她需要通过艺考进入大学的时刻,如果面试的考官们听不懂她说话,她可能会上不了大学,她这才主动让妈妈帮她寻求语言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