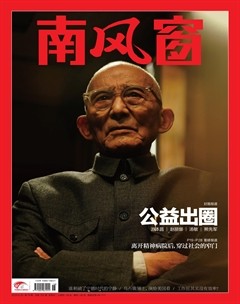2018年7月,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和母亲接连确认罹患“世纪之症”:母亲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初期,刘绍华患了淋巴癌。
一个家庭当中有两个人同时生病,对家人打击重大,家中混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生病的人不好过,没生病的人也不好过”。
然而此后数年间,刘绍华却在与母亲“共病”的经历当中,在照护与被照护的体验当中,获得了更为丰富和富有意义的生命体会,正面的、负面的、坚固的、新生的、美妙的、创造的,“没生病的人很惊奇,生病的人更惊奇”。
度过那段与母亲生命共同下坠的交会时间之后,刘绍华将自己的回忆和感悟,写成了《病非如此》,简体中文版于今年7月出版。
在这本书里,刘绍华记录了与母亲的关系变奏,也重思了疾病与人生的关系。书中的疾病体验,并非单纯指向某种确切的疾病甚至重症,而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出现的困顿和艰难,关乎我们如何在困境中重寻生活的意义感,直至能够坦诚无畏地与自己对话。照护与被照护,也不一定出现在疾病的语境当中,而是每个人对他人的接纳、共情、理解。
8月,南风窗联系到刘绍华。采访安排在20时,刘绍华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听起来并不疲倦,依然很有活力。此时已经是她康复的第六年,她笑着说,如果我不主动讲,没有人看得出我生过病。她说起话来有一点绵柔的台湾腔,却又坚定,不乏机锋。她小心沉吟,为自己的表达寻求最准确的词句,话语之间有坚硬的逻辑,也有温柔的慈悲。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经历过这一切的刘绍华说,她到现在对她的新生活都非常满意,心满意足。
人到中年,经历病痛,却接近了生命的圆融,何以如此?以下是记者根据刘绍华的讲述和书中内容所做的重整。
意义的青黄不接
我其实算很幸运,淋巴癌可以说是重症里的轻症,而且我发现的时候还很早期,所以住院的时候医生都不怎么来管我的,他们总是有更紧急的病人要看管。真正困难的时期,只有治疗的那半年。当时我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其实都不是疾病本身带来的,是治疗带来的。
用化疗的办法杀死癌细胞,也会带来副作用,这个过程病人的免疫力会下降,心情也在承受着压力。治疗结束之后,一个月内,我就很明显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在恢复,这个阶段我称为康复期。
所以我有两个阶段需要跟自己相处,一个是我怎么接纳困难期的自己,一个是康复之后我怎么去跟自己相处。
在生病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心情低落,失去了意义感,我称之为“意义的青黄不接”。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心理上极度困顿,当然身体也被折腾,但是你知道医学在进步,你可以仰赖它,身体会慢慢好起来,可是心理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调整。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上山下海,不管是做研究还是在社会上的参与、跟别人的互动,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但是生病让我体力衰弱,治疗让我的社会关系暂时缩窄,参与社会的程度大为降低。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似乎无所凭依,内心出现虚无感,有朋友说我,差不多是处在一种类似于“突然被迫提前退休”的状态里。
寻求意义的媒介或者说管道,在我治疗期间,出现了断裂。重视公共性的自己,太熟悉跳脱自我、与庞大世界联结的感受和意义,却不知道怎样建立直接的身体感受,真正与自己独处。
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我原本以为的意义感上的话,一旦原先的那种可能性被剥夺,我接下来的生命意义要从何而来呢?
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我原本以为的意义感上的话,一旦原先的那种可能性被剥夺,我接下来的生命意义要从何而来呢?在我没有办法现身实体地跟世界对话的时候,我能够因为只跟自己对话而依然心满意足吗?这个时候,我感到我过去对意义的理解是单调而不周全的,而新的意义感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我会说,那时自己走进了青黄不接的阶段。
这种孤独和困顿,在每个人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生病给了我一个相对极端的情况,去思考人应该如何在困境中安顿身心。假如没有生病,我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件事,但我生病的时候刚好在中年,等于在人生的中场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一开始是被迫进行,我开始学着去做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