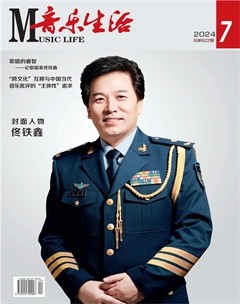笔者从学生时期就关注孙文明,并开始对其二胡艺术进行研究。春秋更迭,教学演奏二十余载,然孙文明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似曾神交。他的乐曲读解、技术诠释、乐谱寻绎等问题,时时牵动着我,尤其是对孙氏音乐行为之根由的思考,从未停止。总的来说,孙文明的二胡艺术有血有肉,他扎根生活却又能超越生活,这与当下盲目炫技、缺失韵味、忽视传统等种种二胡演奏上的迷失形成鲜明对比,却又不自知,现状令人堪忧[1]。
一、离奇的身世和精深的艺术造诣
孙文明(1928—1962),民间盲人音乐家,浙江上虞人,四岁时因患天花而双目失明。十二岁时母亲去世,迫于生活,早年以算命维生,为招揽生意开始学拉二胡,从模仿着拉奏,到善于吸收民歌小调,各类戏曲曲艺无所不学,样样都能激发起他的浓厚兴趣。
随着演奏技艺的精深,孙文明逐渐走上民间音乐家的道路,并开始创作。孙文明的二胡演奏艺术富有创造性,并能根据乐曲表现的需要采用独特的多种定弦。他的作品有无千斤的《弹乐》《夜静箫声》;双马尾八度定弦的《人静安心》《送听》;单双马尾同度定弦的《送春》;双马尾五度定弦的《二琴光亮》;双马尾八度五度定弦的《志愿军归国》;五度定弦的《春秋会》《流波曲》《四方曲》《杜十娘》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孙文明在江苏南京等地参加会演,受到好评和社会关注。1959年应上海民族乐团的邀请,到上海传艺,后又到上海音乐学院授课。这么多未曾见过的二胡技法,让人眼花缭乱,我们不禁会问,孙文明是怎么想到做到的?如果说一个人在书香门第,接受传统文化和新学教育后,成为专家学者或者大学老师,不足为奇,比如当时的刘天华,而不被了解的民间盲艺人孙文明,却站在了中国一流音乐学院的讲台上,还带着自己的作品登上国家的舞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这不能不让我们深入思考。孙文明创造性地运用无千斤、多种定弦、双弦双马尾等“反传统”的演奏方式,是用音乐表达内心,在声音色彩上对接生活,更是本能地对接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夜静箫声》就是孙文明偶然发现弓子没松香时,奏出的音色竟然与箫接近,惊喜不已!孙文明并不急于擦松香,而是找准那个儒雅的声音,创作出新的乐曲。当乐器的物理条件不足时,还能开拓出表达新天地,这是怎样的艺术思维与创作激情?箫的音效,成就了孙文明在中国近代二胡史上创造的声音奇迹。为此还有人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如孙以诚的《如何演奏〈夜静箫声〉中的箫音》;静恩涛的《〈夜静箫声〉中箫声的发音原理》等。这些乐曲和演奏技法,尤其是去掉二胡千斤,成就了孙文明在中国近代二胡艺术发展史上的奇迹。
孙文明使用的二胡琴杆长、把位大、没有止音垫。他借鉴粤胡的演奏方法,将琴筒置于两腿之间,演奏时可以灵活调整夹琴的高度。这样的用琴,这样的操琴处理,增大了表达空间和控制难度。就目前所见,孙文明在一把二胡上实现千斤、定弦、运弓等技术的自由转换,是绝无仅有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