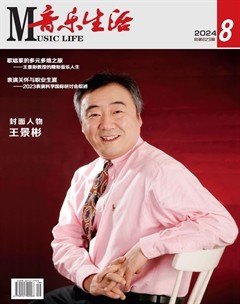晋剧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之一,20 世纪初在山西晋中一带被称为“大戏”,在山西境内、尤其中部地区广受欢迎。既为大戏,学界在不同角度给予了较全面的关注与研究。晋剧唱腔音乐作为剧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第一,对人物唱腔的分析,主要从流派特点、发声特点、演唱技巧、演唱经验等角度,对歌唱部分予以阐述。第二,从创作角度出发,可以是创腔、作曲的创作技法、创作手段,或是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创作作品的解析,重点在于解构作曲技法,激发推进创作更新。第三,对传统唱腔用于不同体裁作品的解读,对不同音乐素材如何在作品中融合、拼接、碰撞等进行个体研究,寻求晋剧音乐在不同音乐乐种中另辟蹊径的发展与传承。第四,是对唱腔音乐的形态分析,其涉面广泛,可涵盖唱腔、曲牌、锣鼓,并可细化为过门、拖腔、花腔等,从逻辑结构、腔词关系、创腔布局、历史衍变等多维角度作出深入剖解,这类研究细枝末节分类诸多,需要研究人员熟练掌握剧种音乐以及相关作曲技法才能得出较为夯实且条分缕析的基础性结论。更为关键的是对谱面所作的大量案头工作,使结论紧密结合于舞台艺术实践中。因此,此类分析应是本学科研究的重点。
一、润腔发展述评
“‘润腔’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话语概念”[1],是润色旋律、纠正字音、烘托戏剧气氛的重要手段。它广泛存在于传统音乐的各类表演中,不仅表现在有字腔结合的各种歌唱型音乐体裁中,还大量出现于各种民族器乐曲中,如古琴中的“吟猱绰注”、二胡中的揉弦等,皆属润腔范畴。从《润腔在古诗词艺术歌曲中的意义及应用》,到《王立平〈红楼梦〉声乐作品古典韵味与润腔分析及实践》,再到戏曲中《龙江剧名家白淑贤的润腔艺术》等,形式多样、角度广泛的研究可以基本推断出润腔丰富的研究状态。
晋剧润腔研究相对滞后,可查论文最早见于2016年樊凤龙所写《润腔及其在晋剧唱腔中的运用》,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润腔的多种形态。晋剧润腔论著较少,关注度较低,与作为大戏的晋剧不相符。
爬梳戏曲润腔和传统音乐润腔的相关研究中,《“润腔”概念由来考——从“甩腔”“小音法”说起》引起了笔者极大地兴趣,其详细论述了周大风的“要腔”“用腔”与徐兰沅“音法”与“小音法”。“小音法”即梅兰芳创腔和演唱中所用的各种唱工技巧中(如挑音、颤音、压音、加装饰音等)修饰、润色的手段,徐兰沅称之为“小音法”[2],也就是我们所用的润腔技法。纵观晋剧发展的近两百年间,舞台上出现过丁牛郭冀四大名家,艺人新秀后辈叠出,但鲜有较为系统的对艺人声腔的理论性总结,也没有定性的流派传承,没有得出同京剧一般对唱腔旋法、调型、腔型和乃至流派唱腔的专业研究,实属缺憾。而“小音法”正字和润腔的技巧却在与梅兰芳同时期的丁果仙唱腔中大量存在。润腔中广泛吸纳有倚音、波音、滑音等各种对唱腔旋律或字音的精细修饰,这些微小的音值、或长或短、或早或晚、或前或后、或屈或伸,使唱腔呈现出行当、角色、心境的独特形制,将谱面由“死”生“活”。而这些在晋剧唱腔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挖掘与总结。
对润腔的认识,很多人认为是对唱腔润色,这当然无需置疑。这种润色往往停留在对唱腔的装饰上,如“装饰音”或“小音法”等,也就是润腔支脉下的装饰性润腔。利用诸如倚音、波音等装饰手段对骨干音进行加花修饰,即是润腔。这一概念出自1984 年《中国音乐词典》对润腔词条的界定(润腔,即加花,民间音乐中使曲调变化的手法),但很快被1989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的润腔词条所修改,其“释义为:‘对唱腔加以美化、装饰、润色的独特技法。’”[3]这足以见得润腔功能不仅仅于此,其早在于会泳的润腔论述中流传下来,《腔词关系研究》中说到的“装饰型”“力度型”“音色型”“速度型”,应该是润腔的基本形态。
二、润腔的基本形态
1.以音高为依托的旋律性润腔
之前提到,戏曲润腔的最基本形态,也就是人们常认为的润腔即是旋律性润腔,这种润腔大都建立在基本音基础上,由其为依托进行润色,以改变字音调值走向、加强剧种特点,形成流派性人物的特种腔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