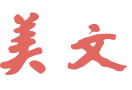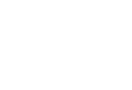一
瓮岭古道,我已来回走过五次了。没走之前,我就想写一点有关瓮岭的文字,可十一个年头过去了,我竟还没动手。
近十多年来,我所到访过的深山峻岭,已数十处吧,但瓮岭是最厚重、最博大的。它最可书写,但至今却无人书写,我的这支笔能对得起它的博大与厚重吗?
2008年的那个将近年关的夜晚,三哥郭文锁在我家小酌。酒饮半酣,三哥又提起瓮岭,又说起当年的瓮岭惨案。
三哥的母亲就是当年惨案的见证者。三哥从小常听母亲讲惨案的经过,他脑海中常不时地再现当年那些年轻的生命惨遭杀戮的情形。可当他长大后,翻遍涉县所有的文史资料,却没找到关于瓮岭惨案的一丁点儿记载。那可是三十多个风华正茂、意气奋发、有血有肉的生命啊!
三哥说,他一定要走一趟瓮岭,去亲近一次那染有烈士热血的泥土,去抚摸一下那两棵见证了烈士牺牲的榔树,去感受一场那裹挟过烈士怒吼的山风,然后写成文字,让后人永远铭记当天那轮带着血色、迟迟不肯下山的夕阳。
当时的三哥,还只是在涉县步行街一个卖儿童玩具的,却谋着“肉食者谋之”之大事。我不禁被感染了,于是决定寒假中陪三哥走一趟瓮岭。
瓮岭,是涉县东南部一座高山,界于清漳河和浊漳河之间。当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属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以瓮岭为中心,驻扎在黄岩、固新、昭义、大丰、东峧、后峧等村,与当地民众相濡以沫,浴血抗日,其事可歌,其情可泣,在中国抗战史上挥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瓮岭,是太行山的一条支脉,它像一条巨龙,从太行山的主峰皇后岭蜿蜒西来,不时地向南北伸出大大小小的“触角”,每一个“触角”上,都佑护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村庄。
瓮岭,也是太行山的一处咽喉之地。瓮岭上有一条古道,南接岭南大巷、东峧,再向南,越过滔滔的浊漳河,就是莽莽苍苍的豫北山脉;北衔昭义、固新,溯清漳河直达太行山腹地,也可越河过皮岭直通华北大平原。瓮岭上的羊肠支道,如遍布它全身的毛细血管,更是四通八达:登临峰顶,向东而下,可达大丰、西达,出武安、磁县,直抵京津要枢;向西,可下西峧、后峧,出平顺、长治,可通三晋大地。
二
瓮岭古道南侧接近东峧的一大石上,有林县香客勒石记载:明成化年间集资捐物重修进香路。这是一条河南信徒赴涉县娲皇宫进香朝拜的路。可谁知在这条祈福禳灾的路上,竟发生过一场绝人寰、泣鬼神的惨案!
半个月后的正月十四下午,我骑车来到瓮岭脚下昭义村的三哥家。那时姨夫和大姨还健在。两位老人听说我俩要走瓮岭,都很吃惊。
大姨又讲起了当年的惨案。当年,她仅十岁,在瓮岭一侧的刘家凹亲耳听见了瓮岭的枪声;事后,站在瓮岭山顶山神庙前的那两棵榔树下,又亲眼见了那些年轻人的尸骨。
姨夫说,他年轻时可没少走过瓮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县城印染厂,东风药厂的工人拉练走瓮岭时,都是他带的路;瓮岭上十里,下十里,上下瓮岭一趟,许多年轻人的腿就肿了。姨夫还担心三十多年了,早已无人再走的瓮岭,经过1996年的那场大雨,瓮岭古道还在吗?
正月十五的早晨,天阴沉沉的。临行前,姨夫让我们带上一把镰刀,又递给了我们几把鞭炮,再三叮嘱进山时要不时放几个,有东西听到了,会躲躲。我知道老人所说东西是什么,它不仅仅是近年来山里已出现的野猪。大姨递给我俩几袋祭品,说路上几处山神庙要拜拜。
我们出了村,走了很长的路,还能听到村人祈福的鞭炮声。
当鞭炮声渐远渐无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小井儿的地方。路左有一青石,大如碾盘,形如雄狮。路右,与青石相对之处,原先也有一巨石,色白,形如奔象。村人说此地雄踞青狮白象,瓮岭内必有一穴好地。可惜五六十年代,村里搞水利建设,白象被毁。现在只有青狮站立在那里,孤零零地细数着叶落花开的岁月。
小井儿这个地方,当年是一家车马店。进京北上的学子,或者是来娲皇宫进香的香客,下了瓮岭,常进店歇脚,准备下一段路程;南下的商客和谪宦,要上瓮岭了,也要进店喝口茶,补补上山的力气。
当年白象所立的地方,现在松柏森森,隐隐约约中还有一间小庙,庙前有新落的红红的一层炮屑,庙里的神灵还享受着人间的香火。
青狮的背后,就是当年车马店的建筑。房顶大多坍塌,但从那断壁残垣来看,这家车马店当年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几处还完好的门楣上,张贴着红艳艳的对联,给这云雾封锁的深山带来一丝意想不到的喜庆。
三
离开小井,没走几步,从那断壁残垣中传来的几声牛哞,透过光秃秃的树梢,在山谷间回响。当年喧嚣的客舍,已成了养牛的场所。历史的变迁,可见一斑。
哞声渐远,我们来到一个叫“三岔路口”的地方。这里有三条路:正沟正上,就进了瓮岭;向东顺另一条沟而上,越过岭可到大丰村;向西也进一条山沟,可上到刘家凹和当地有名的石堂岩。
石堂岩是一个有几处天窗的天然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