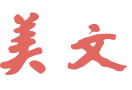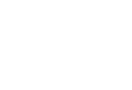仲夏炎炎,幼雀般蜷缩着的小学建筑群矗立在雾青的山野之间,蛙鸣与蝉吟在其中此起彼伏。
沿着知春路排排翡翠色的松柏向前,脚下烘干的柏油路代替了记忆里潮湿的泥土。
正值暑期,成群结伴的孩子早已嬉闹着下山去了。
遥遥望见矮矮的门卫室外,安详的身影躲在阴影里,卧在咿咿呀呀摇晃着的躺椅上,悠悠然晃着手上开了点小叉的老式蒲扇。
“阿爷!”
心底的声音迫切地顺着酸涩的喉舌冲到闷热的气流里,我兴奋地朝着昏昏欲睡的老人扬起手,蹦蹦跳跳的,打破了午间的静谧。
热切的呼喊在冷清的校园门前显得突兀,陈大爷醒了醒神,有些困惑地直起上半身,张望着这个奇怪的有些面熟的青年女孩。
他的背后,五星小学的红旗高高升在钢杆之上,亦如孩童时的崭新与闪亮。
“小娃娃,学校放假了喔,前面向右有路下山去。”待我跑近了些,他眯了眯眼,带着熟悉的慈爱的神情笑笑,又垂下头慢腾腾地整理有些褶皱的灰色的旧衬衣。
倦鸟归巢,一瞬已是四五年,他也误以为是哪家的小丫头片子走错了山路。
双手不自觉地别在橙色的衣衫后,我三步并作两步地立在他跟前撇了撇嘴:“陈爷爷,不记得童家小孩了?”
“童家……下街头童家糕点,童家军你爷爷喔?噢哟啊,珍珍是不是?”岁月催人老,阿爷还是精神矍铄,中气十足的模样。他摸索着记忆记起我,也有些高兴地把蒲扇放下,站起身来。
“是喔!阿爷,回家了,来学校看看。”曳着盈盈的笑,我点了点头,把手里握着的其中一盒家里的绿豆糕递过去。
“谢谢珍珍啊,是放暑假回来的哇?乖乖,个子蹿恁高,跟童老头一样长。”他接过去,赞许地拍拍我的肩,“哟,给你开门哈……”
阿爷转过身去,迈着稳稳的步伐进到保卫室去。
“哗啦啦——”铁栅栏缓缓地拉开,尘封的时光像吻在屋脊上的明媚的阳光,倾盆而下,落在身上有暖烘烘的美好的味道。
他探出头来,笑眯眯地示意可以进去。
直走,也不需弯曲环绕,还是几幢教学楼,一个小操场。
水泥路换成了大理石的材料,小厕所周围的杂草修得平整,绿茵场也重新粉刷了明艳艳的红,炽热的颜色蒸腾着周边灰黛的屋瓦,像是燎原的烈火一直烧到教学楼锃亮的外壳。
远远望着,用来练习跳远的沙坑旁是两个紧紧靠着的天蓝色柱子、明黄色凳子的秋千,油漆也是新刷的。
四周都是山,太阳带着暖,却也不至滚烫。
手表上显示的是下午一点钟,是上学时午休结束的时刻,叮铃铃的铃声在心底响起。
从操场能望见路边的竹林簌簌,是从知春路上下来的必经之路。
我在秋千上坐下了,轻轻地晃着,等杨柳从山上下来。
静默间,想起前几日,跟随父母从外地归乡,灰色的大巴像一只笨拙的异兽,慢吞吞地向前爬着绕着,大嘴吞吐着几十个风尘仆仆的异乡客。
阿爷接住我们繁重的行李,黝黑的脸庞被夏天的热浪刮得红彤彤的,阿奶牵住我的手,手上的膏药和茧子摩挲着我光滑的肌肤。
家里的堂屋糕点码得整整齐齐,用来蒸老式蛋糕的机器“叮”一下响了,灰暗的红灯转为明亮的橙光。
抓了热烘烘的蛋糕吃,我蹿进小时候的房间,钻进铺好的晒得暖暖的被窝,是熟悉的安心的味道。
隔天去镇尾散步,芦苇荡之上架了石筑的大桥,到镇上的小卖部去看,装了统一的牌匾,多了好几家文具店。
走到镇头往山上看,泥路修成了柏油路,一圈又一圈,绕着高山盘曲蜿蜒,户户人家的袅袅炊烟由近及远直至缥缈无边。
躺在床上的时候,挂念的思绪总是飘得远,飘到山上——杨柳的家里。
“阿奶,还记得杨柳不啦?”仰头盯着灰白的天花板的某一处,我轻轻地问。
她是生长在我儿时记忆的一抹清凉的亭亭绿竹,带着独特的安静与美丽。
阿奶戴着老花眼镜,在小沙发上慢慢地用针线织着什么,没犹豫地点了点头:“记得的啊,小时候和你玩那个,住知春路那山上的小女娃。”
“她还跟她阿奶住不?”我迟疑了一会,只问出个最无关紧要的问题,脑海里不自主地又开始勾勒四周土黄色的墙壁和那硬硬的床铺。
离乡的那个假期,装在摇摇晃晃的小三轮里,我到她阿奶家里住过一晚。
只是彼时太娇纵任性,盯着屋外头光秃秃的树,屋里头没有玩具,只有桌椅,还有瘦瘦的小小的低着头沉默的杨柳,我闹着又要下山去。
来是我任性地要来,去也是我哭着要走。
狭小的床铺上,她默默地拉住哭得干涩的我的手,似乎想说些什么。我哭累了,沉沉地睡过去,隐约间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
次日天光乍现,阿爷轰隆隆的摩托车声和混沌的尾气里,我扭过头去,只看见一个黯然的身影在门口光秃秃的树下冰凉石头上木木地坐着,慢慢地变成小小的黑点,和高大巍峨的山融为一个整体。
做孩童的时候我只知道玩耍的乐趣,直到稍大一些,想起杨柳,她背对着大山坐在那棵瘦弱的小树下,听见的是亲人分道扬镳的吵骂声,皮箱拖拽着轧着山路的告别声,看见的永远是抛弃离去。
彼时,轮廓不清的小小身影伴着无尽的悔恨和懊恼,如刀片一般钝入我心。
“不然嘞,她父亲待她又不好。不过去年她好像上了县一中噢,住学校里了。暑假估计也回来的。”阿奶说到她父亲的时候,眼里闪过嫌恶,又继续道,“她阿奶前些日子说要下来买点糕点的,你们要是想见见可以问问。”
“嗯……好。”我呢喃着,想着杨奶奶要早点来,又沉沉坠入梦里去。
也许是我的期盼被上天听到,隔天,身着亮绿色短衫的杨奶奶就笑得敞亮,一脸喜气地推开了我家檀红色的大门,夏天的热风吹开她脸上的皱纹,盛开着绿衣上鲜艳繁复的花纹。
不一样。和记忆里愁眉不展、佝偻着的苍老身影不一样。
“杨阿奶,精神不错啊,身体啊好呀?”阿爷热情地给她称了老式蛋糕,又拿了月饼作赠,忙不住挡了推辞。“拿回家尝尝吧,也给杨小丫头,都不容易。”
“那谢谢啦,她假期回来的,珍珍也回来啦?我明个叫她下来找你玩玩,一天到晚闷在家哪像话。”杨阿奶望见了在偷偷往嘴里塞绿豆糕的我,一边笑说着,一边把阿爷手里的东西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