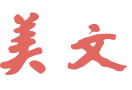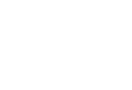一
记忆是一坛酒。
有些人、有些事,只有酝酿了一段时间,才能感到它的绵甜和醇香。到惠农工业园区去采访的时候,按习惯,我一定会去看那条河!那条河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河。细算起来,我已在它的身畔生活了30年。前15年我与它日日相伴,耳鬓厮磨。后15年,我离开它到45公里外的另一个区,与一座山生活。
到河边去,登临大桥,或在河流的臂弯里静坐。不呼朋,不唤友,任清风拂面,任暖阳包裹,任萦洄激荡的河流奔腾北去,是我生命中最惬意的事情。
作为中国人,有一条河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那就是黄河。我永远无法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在老家瓷厂的一间单身宿舍里,张主任跟我讲了他的一次旅行,确切地说不是旅行,是参观。张主任是企管办主任,他随厂里的一个参观团到宁夏石嘴山瓷厂去学习,回来后打了鸡血般亢奋。宿舍很小,进门就能看见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床前右手边放着一张三抽桌子,两边卡着两张椅子,桌子对面是一个书柜,张主任高大肥胖的身体在桌子和书柜中间游走,脑袋微微前伸,一只手掌扣在半边脸上,指缝里夹着香烟。他很亢奋,说那家瓷厂的规模,说那家瓷厂的管理,然后说到了黄河,说厂子坐落在黄河的臂弯里,地理位置很好,前景一片璀璨。
他说到黄河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像有一只手拨动了时间的钟摆,有一只鼓锤锤响了尘封的鼓面,一扇窗被打开了,一抹明丽的阳光照射了进来。从小到大,在课本里,在文学作品里,在新闻里,我曾无数次遭遇过黄河,都没有这一次那么临近。在书桌上那盏晕红的台灯下,张主任的每一句话都挟裹着黄河的气息。作为一名陶校毕业生,那一阵,我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寻找出路,没多久,我调了进去。张主任自己可能也没想到,那个晕红的夜晚,他充当了我的精神导师,他把一个厂子交给了我,也把一条河交给了我。一直静卧在我的血管里的那条河奔腾了起来。后来,我与张主任千里相隔,只见过一次面,我所在的瓷厂也破产了,但与那条河一直相伴至今。
二
那时候的交通条件还很差,我坐了一夜汽车到银川,第二日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中巴才到了石嘴山,放下行李,不顾疲惫,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黄河边。我只有23岁,我的人生正在启幕,充满了渴望和未知,总觉得生命应该比拥有的更精彩,我在努力寻找着生活的捷径,我甚至想面对黄河的时候一定会顿悟些什么。沿着城市仅有的那条街道一直向北,猛地就看见高高的桥基像一堵城墙,上面刻满了浮雕,从大禹治水到城市解放,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中国简史。浮雕似乎在告诉我,黄河不仅挟裹着泥沙和岁月,也承载着历史,中华文明从这里启航。大桥与街道同向,还没看见黄河,就强烈地感觉到心中的那条河如一个孤儿,苦苦寻觅了多年后,终于找到了母体,汩汩地汇入了地理的河流。我急切地沿着折线般贴在桥基上的水泥台阶三步并做两步地奔上去。
黄河!我终于看到了你,终于站在了你的身边!那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清晰地看见那条河静卧在我的面前,水的来处,太阳在厚厚的云层后面发出白亮的光晕,水面上菱形光斑由远处铺陈到脚下。水的去处,灰色的云层如一团棉絮,把涓涓流水吸纳了进去。河面上,一些水鸥在滑翔和起落,远处的滩头上,一位渔者正把网撒成一朵朵美丽的喇叭花。这里的黄河,并没有李太白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奔腾之气,在广阔的宁夏平原上,它娴静如淑女,在河滩上尽量延伸着臂膀,舒缓宁静地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我的脑子有了短暂的空白,只是与它凝视着,凝视着,然后,迈步向桥中央走过去。我走得很轻很慢,生怕惊扰到它。站在大桥中央,就站在了黄河柔软的腰身上,耳边的清风掀动了我的头发和衣角,呼呼作响。那是吹过千年的风啊,挟裹着多少历史烟云和伟人情怀,现在,它正抚摸在我的脸上。我似乎一下变小了,脆弱了,只是那么顺从地亲近它,感受它。我的南边是那座我即将开始生活的小城,我看见亮灿灿的阳光下冒着白烟的高耸的烟囱,滨河大道上一辆接一辆拉着煤炭的车辆走向全国各地。北边是内蒙,目光沿着宽阔的河面扫视过去,攀上河堤就能看见黑黢黢的山脉,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露天煤层,晚上,能看见自燃的火苗四处跃动。
天高地远,长河激荡,每过去一辆车,桥身都会微微颤抖一阵,我忽然觉得整个时空整个生命都在微微颤抖,内心的忐忑油然而生。我不知道,这么贸然地把自己交给这里,交给一条河,是否正确。此后的15年,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15年,我的生活并没如我想象的那样灿烂起来,好在我可以随时去看黄河。那是多么奢侈的一段时光啊!无数个清晨和傍晚,我在大桥或河滩的红柳林中徜徉。黄河是我的,我是黄河的。我唯有黄河,黄河也唯有我。河边旖旎的风光和河面上的清风,见证了我的渴望和萌动,见证了我的青春和爱情。
三
我内心珍藏着的很多珍贵镜头都与黄河有关。
我与妻子相识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们一起到黄河边散步。那时我在厂里任一个小中层,厂子却挣扎在破产的边缘,福利差、工资低、前途未卜,厂里的小伙子们都很自卑,我也一样。妻子在声誉极盛的金融部门工作,我尚不知道她的态度。我试探着抓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躲避,身子向我依了依。一种甜蜜的感动瞬间弥漫过我的全身,就像第一次看见黄河,我斜倚在大桥的水泥护栏上一样。那是个初春的下午,河道中央流凌滚动,两边参差不齐的残冰为河流镶上了雪白的花边。我把妻子的手攥得再紧一些,就有一些温热的东西爬上我的眼帘,世界变得晶莹起来。黄河作证,从此两个生命将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相依相伴,并辔而行。一个夏日的午后,在艳丽的阳光下,黄河岸边的红柳婆娑,我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在河边的黄土路上尽情奔跑。他穿着大红色运动服的身影在茂密的红柳丛林中忽隐忽现,急切而踉跄的脚步切割着时光,天籁的银铃般的笑声划破了时空,在河道里回荡。我和妻子紧跟其后,“小心,慢点”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我们一家人就那么欢快地留在了那条河漫长而纷杂的记忆里,我的浓眉与妻子的笑颜与水面的波光一起荡漾……
著名作家史铁生说,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看来我还算得上一个习惯良好的人,因为我记住了走运也记住了倒霉,那次倒霉要比走运刻骨铭心。我曾千里相投的、承载着我的青春的瓷厂破产了,我的心灵是多么脆弱啊,好像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我自卑、羞怯,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告诉妻子,每天继续坚持去“上班”。我沿着去厂子里的路走一段后,就拐到了黄河边上,找一个坎楞或一簇灌木丛把自己挡起来,然后坐着,愣愣怔怔地看着那条河。我心乱如麻,不知道有多少浪花从我面前闪过,不知道有多少阳光洒向了河面,也不知道河道上空飘过了几朵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