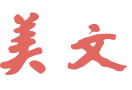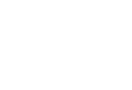气泡一样,从窗帘缝隙冒进来,投射在衣柜拉门上。眯着眼睛看,如同一排排鱼鳞,在衣柜拉门上一朵一朵地浮动着。这入睡之际,隐约闻到青竹鱼的腥气,鱼肉蒸熟后的肉香味。
害羞的,迟疑的,忸怩的,不住在高楼,月光这位城市稀客,绝不会造访我的卧室。五六个小时前的晚餐,我和妻吃了一尾体态臃肿的饲料鱼,现在把月光想象成一尾野生青竹鱼的鱼鳞,大概是肠胃闹了脾气。
青竹鱼是南方珠江水系名贵经济鱼类的一种,查到的学名叫倒刺鲃,别称青竹鲤、竹鲃鲤、青鲋鲤。青竹鱼体肥,抱起来沉甸甸的,能长到十斤以上,五六斤最为多见。它头小,体背青绿,腹部灰白,背鳍、胸鳍、腹鳍呈粉红色,尾鳍青色或粉红。它出没于流动水域,只在清澈而且较深的水环境生长。
医学上说,青竹鱼含有丰富蛋白质、脂肪,还有丰富的硒、碘等微量元素,有抗衰老作用。可那时候人都快饿疯了,哪管它有没有硒、碘,有没有抗衰老作用,人们见肉就啃。十二斤重的青竹鱼就像一头躺在案板上的猪仔,正大口大口地吮气,红色的腮帮一起一落,一副缺氧的疲态。爸爸高兴坏了,他摇了摇青竹鱼的尾鳍,说尾鳍就像铁扇公主手上的那把大扇子,能刮出一阵风来。爸爸喊我摁住大扇子,他要动刀子了。我先摸了摸它清澈的眼睛,滑溜溜的,像攥着一颗翡翠珠子。父亲把刀子扬得高高的,大喊一声,猛地往鱼头击打下去。青竹鱼猛地甩动大扇子,我被弹退了大几步。我说:“爸,它力气好大,我摁不住它。”胸前沾了一摊黏糊糊的它的体液,嘴上也挂着它的体液,用嘴巴咂一下,我舔出了腥甜的味道。父亲将它砍成比我的拳头还大的肉块,然后放进沸腾着的一大锅水,再放入姜和一大勺猪油,一大锅鲜鱼肉很快就生发肉香味。饥饿年代煮什么都好,都是这般潦草,食材却出奇有味。家族里的叔伯来了,邻居家的彩姨、三爷也来了,按量每人分得一碗,我分得鱼背上的一块肉和一块胸鳍肉。白花花的鱼肉裸露在碗里,圈圈点点的鱼油在碗里荡来荡去,口舌和胃即刻骚动起来,仿佛一场盛大的交响音乐会,遏制不住地澎湃。吃下这碗鱼肉,身体很快热乎起来,发际间渗出了许多热汗。我和妹妹因为营养不良而贫血,这碗鱼肉帮助我们养回了不少血气,妹妹舔着碗说:“爸,再去打一条回来吧,我还想吃。”那时候,爸爸非法购买炸药,炸鱼。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出门去接廖哥,他正拿猫哄女儿跟她妈妈待一块。猫从他手上逃开,跳到屏风上叫。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家处在紧张的对抗里,任何一件有争议的家庭琐事,都有可能成为破镜的导火索。猫这种动物,总能最先嗅到气息。
廖哥说,今天我们换一种策略。
我问,怎么个换法。
今天不走以前的老路,不钓花生米了,今天钓无花果。
无花果怎么个钓法,我没试过。
到河边了看我钓,跟着我钓。
好,出发。
车在山的夹缝,绕着弯要走八十公里。这一趟行程开得不快,估摸着要消耗一整个上午的时间。碰上每一处急转弯,急急地打方向盘,迎面涌上来的都是崖壁。山间的雾气散得慢,就像在眉眼上罩着,只能不停摁喇叭,提醒另一侧来车放缓车速,否则就迎面撞上。
南方的河流,蛇行一般奔突。人们总先撞见群山,然后在群山的间隙用力一瞧,才看到山脚下翡翠绿的河流。这条被称为“黑水河”的河流,给它取名的人该是站在山巅往下瞧,见其倒映黛色的山影,才称之“黑水”。黑水河极清澈,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23年1月至12月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中,黑水河所在城市崇左市排在全国第三,黑水河位列其中。黑水河迂回曲折,大部分盘踞在南疆大地,有一段为中国与越南的界河。
停好了车,便开始寻找无花果。四野无人,万物慈悲,只见寂静的绿。我们就像两只蚂蚁,孤独穿行。
无花果树歪歪扭扭地生长在黑水河边,树冠的一半擎在河岸,一半虎爪一样伸出水面。葡萄一样的果子爬满树干,密密匝匝的,传说果子与榕小蜂存在共生关系,前者为其提供产房,后者为其传粉到其他果实。我赤脚爬上无花果树,像抱住一条巨蟒那样抱住它的躯干,伸出手去抓下一把无花果。成熟的无花果紫红,攥手里一捏就破,如同攥着软糯的丸药——它可能是自然界的丸药,在动物界是生命之果,在植物界,它全年都会结果。廖哥在树下张嘴瞪眼,我朝他的方向抛下无花果,他捡起几颗,用衣角擦了擦表皮,掰开,丢进嘴里品尝其鲜味,也不顾里头有没有榕小蜂或者它的幼体。
青竹鱼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类果子了。廖哥撩起衣袖抹了抹嘴角,他的嘴角被无花果的汁液染成紫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