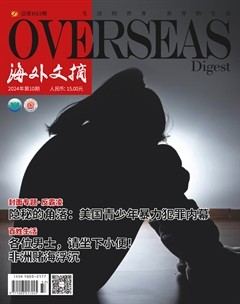隐居青少年
哈丽雅特的两个儿子小时候非常喜欢交朋友,所以她万万没想到他们会进入她所说的“隐居阶段”。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两个男孩开始躲在卧室里。虽然他们热衷于玩游戏,和朋友在网上聊天,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似已消失殆尽。
“他们根本不想见朋友,只想独自待着。”哈丽雅特说。她在小镇上的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担任经理。虽然她不想揪着这件事不放,但孩子们的孤僻还是困扰着她。她建议两个儿子像她年轻时一样,和朋友一起进城玩,但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不理解,既然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为何还要和朋友一起去逛商场?所有一切都鼓励他们宅在家里——手机、游戏、精彩的电视、送货上门的便利服务。
哈丽雅特描述的这种现象,许多青少年的父母都深有同感:这是一种看起来更加封闭、居家不出、发展缓慢的成长方式,有时可能会持续到青春末期乃至二十出头。2024年1月,生意惨淡的夜店巨头瑞克姆公司宣布计划召集管理层应对危机,公司表示,1/3的英国年轻人减少了社交活动。
在澳大利亚,一项调查发现,71%的网络世代(出生于1995至2010年间)减少了外出。最近,出于对“隐居青少年”的担忧,韩国政府提议每月发放490美元的津贴,帮助那些郁郁寡欢、像隐士一样的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虽然“瘫在沙发上”这种现象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身无分文所致,但飞涨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足以彻底解释活动组织“同大于异”2023年12月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该调查显示,24岁以下的英国人比中年人更支持恢复疫情期间的一些措施,比如关闭夜店,禁止六人以上的社交聚会。
外出约会对年轻人来说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他们不出门也能在交友软件和社交媒体上找到伴儿。还有外卖、影视剧和短视频,都能把一整晚的娱乐活动直接送到家。这一代人不似上一代人那样喜欢喝酒,外出买醉也失去了往昔的吸引力。早在疫情之前,英美两国的未成年怀孕和青少年犯罪等冒险行为就在稳步减少,与此同时,在外兼职和拥有驾照的年轻人也在减少——这两样东西曾是通往自由的钥匙。美国心理学家简·腾格在其书中写道,她所说的“焦虑一代”迟迟不能完成成人的里程碑,如恋爱、开车、周末兼职和适应外界,究其原因,在于沉迷智能手机和父母过度保护。
从很多方面来看,年轻人似乎正在遵循我们总挂在嘴边的嘱咐:懂事、不惹麻烦、好好做功课。然而,在育儿网站上,诸如“我家孩子为什么整天待在房里?”这样的帖子却层出不穷,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也许,这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至少,过去的年轻人不这样。
不再外出
周六晚上,俱乐部里人满为患。这里曾是沃平码头后面的一座仓库,此刻却低音轰鸣、激光频闪,天花板上仿佛都要滴下汗水来。我好像能感受到这一切,却又不尽然。因为这场狂欢上演于伦敦东区的超级俱乐部,而我和有些人一样,窝在自家舒适的沙发上,用手机刷着这场狂欢的视频。
年纪轻轻却宅在家里,曾一度象征着社交死亡。但东区超级俱乐部高级运营经理杰克·亨利却无奈地表示,对网络世代来说,这种情况已越来越“平常”。亨利自己也只有26岁,他从小就看着父亲组织老派的狂欢派对,入职俱乐部之前,他也在家乡的夜总会工作过。无论是浩室音乐还是鼓打贝斯舞曲,该俱乐部都有明星级的打碟师,成功在伦敦站稳了脚跟。然而,亨利表示,现在越来越难吸引年轻的会员进门了。若有特别活动,比如亨利在跨年夜组织的30小时马拉松派对,年轻人也会来,但可能一个月才来一次。俱乐部聘请了一名摄像师拍摄店里举办的活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宣传短片。可亨利说,最近,有些人似乎在用观看这些短片替代外出。

尽管俱乐部成功吸引了稍微年长一点的群体——他们的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仍然乐于走出家门——但亨利不禁在想,等年轻的俱乐部会员长到这个年龄时,会是怎样一幅光景。“他们会改变吗?会不再只盯着手机吗?”他说,2023年夏天是这么多年来,伦敦的俱乐部过得最艰难的一个夏天。由于生活成本危机,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下降了。
曼彻斯特是欧洲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