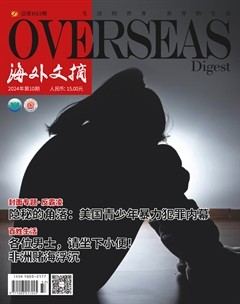过度囤积的危害
在近期一次“囤积问题小组”会议上,伦敦沙德韦尔和白教堂区消防站站长丹尼尔·皮尔森播放了一段火警电话录音。来电人因房屋失火而惊慌失措地求助。消防员立即出动,抵达后却无法进入火灾现场。皮尔森展示了现场的照片:住宅入口和走廊被大量杂物堵塞,已烧得面目全非。报警人死于家中。2022年,伦敦消防队处理了1036起因可燃杂物囤积引发的火灾,共计186人受伤,10人死亡。为此,消防局排查并登记了囤积症患者的住所,一旦这些地方突发火情,将安排更多人力支援现场。
囤积问题小组由资深消防员、心理健康专家、社会福利住房管理者以及住房和环境卫生委员会官员组成。每月一次的会议上,成员们围绕具体案例探讨干预措施:消防员是否应当上门推广烟雾报警器和阻燃床品?是否需要向囤积症患者推荐心理咨询师?房屋管理者是否应强制清理房屋或驱逐囤积过度的房客?面对囤积行为,社会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事实上,小组的成立已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社会对囤积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囤积绝非“东西太多”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需要针对性的政策和精细长远的管理方案。
此前,《英国囤积王》《囤积症患者:活埋》等纪录片和真人秀的热播,让囤积问题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些节目对囤积现象的探讨较为肤浅,认为这只是极少数怪人的行为,且通过大扫除就能解决。事实上,囤积症是一种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影响了全球2%至6%的人口,已成为当代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地方政府官员和社工告诉我,囤积症患者占用了大量医院床位,因为医院不敢让这些人回到危险的住所生活。还有社工提到,在囤积症患者家中帮忙时经常会被掉落的物品砸伤,因此,现在他们会事先要来住所照片,以评估后续工作的风险等级。
2022年,一位政府官员报告了过去几年对某位囤积症患者进行干预的费用支出——总计3.2万英镑,包括强制清理费、房屋维修费、诉讼费等(这还不包括患者搬离住所期间产生的临时住宿费)。该官员主张,发现囤积问题的苗头时便要进行干预,切勿等到危机降临再采取行动,具体措施包括:与囤积症患者建立长期关系,获取信任,逐步改善其囤积习惯。若等到囤积行为随时可能引发安全风险时再干预,一切就太晚了。
囤积症是心理疾病
以往,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通常只有在发现严重的囤积问题时才会介入,对策也往往是清理囤积物,而非从源头解决问题。11年前,囤积症被认定为心理疾病。伦敦国王学院的社会关怀研究员妮可·斯蒂尔斯称,此举意义重大,表明社会对囤积症的理解发生了“根本转变”,对其规模和严重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仅在美国,就有百余家囤积症相关组织,英国也组建了各种囤积症援助小组。然而,理解不等于治愈。
尽管针对囤积症的研究近些年才开始兴起,囤积现象本身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纽约哈莱姆区的霍默和兰利·科利尔兄弟便是早期著名的囤积症患者:1909至1947年间,二人用120余吨杂物和垃圾填满住所,直到邻居报警称公寓楼里有异味,警察才在垃圾堆里找到兄弟俩的尸体。由于他们的极端囤积行为,囤积症曾被称为“科利尔兄弟综合症”。美国东海岸的消防员至今仍习惯将塞满杂物的住所称为“科利尔豪宅”。
1947年,德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描述了“囤积性格”,认为这种性格“倾向于通过不丢弃任何东西来缓解不安全感”。15年后,一位精神病学家将老年人长期囤积杂物的现象称为“收藏家狂躁症”。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开始形成囤积症的诊断标准:囤积且舍不得丢弃毫无价值的物品,居住环境无法满足正常生活,囤积者对其行为感到沮丧等。
2013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首次将囤积症列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类别。同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式认定囤积症为一种心理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指南。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了相关文件。一些精神病学家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原本正常的行为病态化多有不妥,也有人对需要医学介入的囤积程度提出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