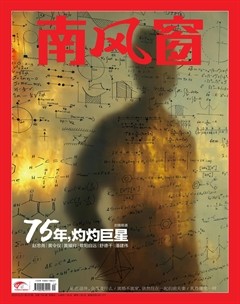合肥,9月,新生入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包信和对2024级“新生”们提出一个开放式问题:创校先辈们为何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学校命名?
在解释自己的答案时,包信和将“中科大”的校名拆开,对应了四位科学家,分别是杨承宗、潘建伟、钱学森和李政道。
“中国”,对应杨承宗,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以中国为首,终身科教报国。
“大学”,对应钱学森和李政道,他们“文理双全”,是全面发展的榜样。
“科学技术”,则对应了潘建伟。包信和解释时,先提到了潘建伟主攻的量子理论,“这就是当今世界最深奥和最重要的科学之一”,他接着鼓励新生向“无人区”进发,追求“高峰要高到九重”……
上述被提及的四人中,潘建伟显得很特别。
他还“年轻”,今年54岁,仍在科研一线冲锋。
此外,他研究的领域“量子信息技术”,常年饱受争议。
量子,一个被各路骗子和“民科”用坏的词,给了科幻和“民哲”们太多胡搅蛮缠的空间。潘建伟曾说,科技创新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别人都说你不靠谱”。
这话令人不觉辛酸。
第二阶段,有一定成果,又有人说“理论上可行,但属于基础研究……实现工程化还有一定距离”。1990年代,与潘建伟一起做“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的一位同学说,他们在有生之年不会看到这项技术落地应用。
曲高和寡。很长时期,量子信息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因为过于前沿而少人问津,称之为“无人区”并不夸张。
第三阶段,苦尽甘来,“技术被广泛使用后,大家会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项技术已经不够新了”。
今天的量子信息技术,处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它不再是“无人区”,而是被认为能够撬动数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与AI一起被看作“下一代革命性技术”。风口当前,世界发现,潘建伟为代表的中国量子信息“新势力”,站在最前边。
这正是包信和院士提到的,进发“无人区”的意义。
潘建伟的科研历程,代表对中国大科学家的一种新的叙事:今天,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在重大领域做着原创性的探索,并且领先于世界前沿。
好奇的少年
量子理论,前沿、晦涩,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连爱因斯坦也无法接受量子理论的某些“原理”。
最著名的例子有两则:一是关于“量子叠加”,是说量子某些自身特性,会在被测量时,因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又或者因测量而改变,即所谓“坍缩”。爱因斯坦不认可这样的“特性”为量子的自身特性。另一则关于“量子纠缠”,爱因斯坦认为它违背狭义相对论,因此不合理。他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